错认罪妻:总裁追妻火葬场(顾夜寒楚兮)小说免费阅读无弹窗_完结小说错认罪妻:总裁追妻火葬场顾夜寒楚兮
时间: 2025-09-16 01:17:23
傍晚的时候,夕阳把落剑村的天空染成了一片橙红色,云彩像被点燃了一样,透着暖融融的光,把村里的土坯房、老槐树都镀上了一层金边。
林澈挑着一担柴,慢慢往村里的杂货铺走。
这担柴有六十斤,比平时多了十斤——早上从剑馆回来后,他没歇气,在老林里多劈了一个时辰。
一是想多赚两个铜板,好早点攒够下次报名的学费;二是想让自己累一点,这样晚上躺在炕上的时候,就不会胡思乱想,不会再想起周铁山的轻蔑和学徒们的嘲笑。
他在肩膀上垫了一块粗布,可六十斤的柴压上去,还是勒出一道深深的红印,从棉袄里透出来,疼得他每走一步都忍不住皱皱眉。
汗水浸湿了他的后背,棉袄里面的衣服都粘在了皮肤上,风一吹,凉得他打了个哆嗦,鸡皮疙瘩又起来了。
他走得很慢,每一步都很稳,眼睛盯着脚下的路,生怕柴捆掉下来——这担柴是他一下午的心血,劈的时候胳膊都抡酸了,要是掉了,不仅赚不到钱,还得重新劈,今晚就别想睡觉了。
走到村中间的巷口时,林澈停了下来,想歇口气。
巷口有一棵老槐树,树干得两三个人才能抱过来,虽然冬天里叶子都落光了,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桠,却依旧透着股老劲,枝桠在夕阳下投下长长的影子,像一条条黑色的带子铺在地上。
他把扁担从肩膀上卸下来,靠在槐树上,揉了揉肩膀——红印的地方一碰就疼,他只能轻轻按揉,缓解一下酸痛。
就在这时,一个嚣张的声音突然从巷子里传了过来:“哟,这不是想当剑修的劈柴小子吗?”
林澈抬头一看,只见三个少年从巷子里走了出来。
领头的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年,穿着一身宝蓝色的锦缎衣服,腰间挂着一块白玉佩,玉佩上刻着个“周”字,手里拿着一把新的木剑,剑身上还刻着精致的云纹——那是周铁山的侄子,周虎。
跟在周虎身后的两个少年,也是青岚剑馆的学徒,穿着统一的青色学徒服,手里也拿着木剑,脸上满是讨好的笑容,眼神却透着挑衅,像两条跟在主子身后的狗。
林澈不想惹麻烦,他低下头,把扁担往肩膀上扛,想绕开他们走。
可周虎却快步走过来,伸开胳膊拦住了他的去路,嘴角勾着一抹坏笑:“怎么?
看见我就想走?
早上不是还去我姑父的剑馆报名学剑吗?
怎么,被我姑父赶出来了?”
林澈没说话,侧身想从周虎旁边绕过去。
可周虎却突然伸出脚,狠狠踹在了他的柴捆上。
“哗啦!”
一声响,柴捆一下子倒在了地上,干柴滚落一地,有的滚到了巷口的路上,有的滚进了旁边的泥水里——中午的时候下过一场小雨,巷口有个低洼的地方,里面积满了泥水,黑乎乎的,还漂着点草屑。
“哎,你干什么!”
林澈忍不住喊了一声,声音里带着愤怒。
这担柴是他一下午劈的,现在撒了一地,有的柴还断了,怎么向王大叔交代?
怎么换今晚的饭吃?
“干什么?”
周虎冷笑一声,走过去,用脚踩住一根滚到他脚边的干柴,脚尖轻轻碾着,柴杆发出“咯吱、咯吱”的声音,像是要断了。
“我姑父没告诉你吗?
让你别再想学剑的事,好好劈你的柴。
你倒好,还敢往剑馆那边凑,我看你是不长记性!”
林澈看着那根被踩得变形的干柴,心里又疼又气。
他攥紧了拳头,指甲嵌进掌心,疼得他清醒了点——他不能动手,周虎是周铁山的侄子,要是打了他,周铁山肯定不会放过他,到时候别说劈柴赚钱了,能不能在落剑村待下去都难说。
他深吸一口气,压下心里的火气,蹲下身,开始捡地上的柴。
干柴散了一地,有的滚得很远,他得跑过去捡;有的掉进了泥水里,泥水没到了他的脚踝,冰冷刺骨,很快就把他的布鞋浸透了,冻得他腿发麻。
有一根柴滚到了水坑的最里面,他伸手去够,手指被水里的石头划破了,流出的血在泥水里很快就散开了,变成了淡淡的粉红色,可他没管,只是把柴捡起来,放在一边。
“捡啊,怎么不捡了?”
周虎站在旁边,抱着胳膊,笑着看着他,像在看一只被戏耍的猴子。
“是不是觉得累了?
早知道这样,就别痴心妄想学剑了,安安心心劈你的柴多好。
你看你现在,跟个泥猴似的,多丢人。”
跟在周虎身后的两个学徒也笑了起来,一个瘦高个的学徒说:“虎哥,你看他那样子,跟个乞丐似的,还想学剑,真是笑死人了。
我看他这辈子也就只能劈柴了。”
另一个矮胖的学徒也附和:“就是,剑脉残缺的废物,还想当剑修,我看他是脑子坏了。”
林澈没有理会他们的嘲笑,继续捡柴。
他把捡起来的柴一根根擦干净——没沾泥的就用袖子擦,沾了泥的就放在水坑边的石头上,用石头刮掉上面的泥,虽然刮不干净,至少能少带点水。
捡了快半个时辰,才把所有的柴都捡起来,堆成一小堆。
他找了根绳子,想重新把柴捆起来,可绳子刚才被柴压断了,断口处的纤维乱糟糟的,像被啃过的草,根本没法系紧。
林澈蹲在地上,指尖捏着那截断绳,心里有点慌——没有绳子,怎么把柴挑到杂货铺?
就在这时,他看到了自己的腰间——那里系着一根粗布腰带,是母亲生前给他缝的,灰扑扑的,边缘磨得起了毛,却异常结实,平时劈柴时勒着,能让他更用得上劲。
咬了咬牙,林澈解下腰带。
粗布贴着皮肤的地方还带着点体温,他把腰带铺在地上,先把没沾泥的干柴归拢到一起,码得整整齐齐,再小心翼翼地把泥水里的柴捡出来,用袖子擦去表面的泥,然后放在上面。
等柴都拢成一堆,他把腰带绕着柴堆缠了三圈,每一圈都用力勒紧,首到粗布嵌进柴缝里,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。
最后打了个死结,拽了拽,虽然柴堆看着歪歪扭扭,却总算能挑起来了。
“切,还挺能撑。”
周虎撇了撇嘴,觉得没趣了,“走了,跟个劈柴的耗着,浪费时间。”
说着,他带着两个学徒,晃悠悠地往剑馆方向走,路过林澈身边时,还故意撞了他一下。
林澈没站稳,差点摔在柴堆上,他扶住扁担,稳住身形,看着周虎的背影,眼底的火又冒了起来,却还是硬生生压了下去。
重新把扁担架到肩膀上时,林澈疼得倒吸一口凉气——刚才被周虎踹过的地方,此刻被扁担一压,像有块石头嵌在肉里,连带着胳膊都抬不太起。
他扶着扁担,站了好一会儿,才慢慢迈开步子。
柴堆有点松,走两步就晃一下,他只能走得极慢,时不时停下来,用手把滑出来的柴往里推。
夕阳渐渐沉到山后面,天边的橙红色被暗紫色取代,风也变凉了,吹得他耳朵发麻,脸上的泥水干了,紧绷绷的,像糊了层土。
路过村里的戏台时,几个村民还坐在那里聊天,看到他的样子,有人叹了口气,有人低声议论:“这孩子,又被周虎那小子欺负了吧?”
“唉,没爹没妈,又没剑脉,在村里难啊。”
林澈低着头,加快了脚步,不想听那些议论。
他知道村民们没有恶意,可那些话像细小的针,扎在他心上,比周虎的嘲笑更让他难受——他不想被人同情,更不想被人当成“可怜人”。
终于走到杂货铺时,天己经擦黑了。
杂货铺的木门虚掩着,里面透出昏黄的油灯光,王大叔正坐在柜台后面算账,算盘珠子打得“噼里啪啦”响,声音在安静的傍晚格外清晰。
听到脚步声,王大叔抬起头,看到林澈的样子,手里的算盘停了下来。
“小林?
你这是咋了?
浑身都是泥?”
王大叔连忙走出来,他五十多岁,头发花白,脸上满是皱纹,眼睛却很亮,说话总是慢声细语的。
看到林澈肩膀上的红印,还有手上的伤,他皱起眉头,“是不是周铁山的人又找你麻烦了?
是不是周虎那小子?”
林澈把柴挑到后院,卸下来时,腰带一松,两根柴滚了出来。
他连忙去捡,王大叔也蹲下来帮忙,捡起一根柴,摸了摸上面的泥,叹了口气:“肯定是周虎那混小子干的。
这孩子,仗着他姑父是馆主,整天在村里欺负人,早晚要吃亏。”
林澈蹲在地上,把柴摆整齐,声音有点闷:“王大叔,不怪他,是我自己不小心弄撒的。”
他不想让王大叔为难——王大叔的杂货铺要靠剑馆的学徒照顾生意,要是王大叔为了他去找周铁山理论,以后学徒们不来买东西,王大叔的生意肯定不好做。
王大叔没再追问,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,力道很轻,怕碰疼他:“傻孩子,别总自己扛着。
这天越来越冷,柴不好劈,要是累了,就歇一天,别硬撑。”
说着,他转身回了屋,很快拿了一个白面馒头出来,递到林澈手里。
馒头还带着点温乎气,捏在手里软软的。
“今天柴挑得多,这个给你,比黑面的软和,填肚子。”
林澈愣住了。
白面馒头是王大叔自己都舍不得吃的,平时只有逢年过节,或者他孙子来看他的时候,才会蒸几个。
“王大叔,我不能要,我有黑面馒头。”
他把馒头往回推,怀里还揣着中午剩下的那个黑面馒头,硬邦邦的,硌得胸口有点疼。
“拿着!”
王大叔把馒头塞到他手里,语气很坚决,“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,总吃硬馒头不行,会把胃吃坏的。
对了,前几天你说想去剑馆,怎么样了?
成了吗?”
提到剑馆,林澈握着馒头的手紧了紧,指尖有点发凉。
他摇了摇头,声音更低了:“没成,周馆主说我剑脉残缺,引不动剑元,不收我。”
王大叔哦了一声,沉默了片刻,然后拍了拍他的后背,像拍自己的孙子一样:“没事,咱不学剑也能过日子。
你手巧,劈柴又勤快,以后要是想做点别的,比如跟着张铁匠学打铁,或者跟着我看铺子,大叔都能帮你琢磨琢磨。”
林澈点了点头,没说话。
他攥着温乎的馒头,心里暖暖的,眼眶却有点发热。
他知道王大叔是为他好,可“学剑”这两个字,像颗种子,早就埋在了他心里,就算现在没发芽,也没彻底死掉。
“王大叔,我先走了,明天再来劈柴。”
林澈把馒头揣进怀里,又接过王大叔递来的两个铜板——这是今天的工钱,比平时多了一个,他知道是王大叔特意多给的。
“路上慢点,天黑了,小心脚下。”
王大叔站在门口,看着他的背影,还在叮嘱,“要是怕黑,就喊一声,大叔给你拿个灯笼。”
“不用了王大叔,我能走。”
林澈应了一声,挑着空扁担往家走。
他家在村西的角落里,是一间破旧的土坯房,屋顶漏了好几处,去年冬天还塌过一次,是王大叔请人帮他修好的。
走在路上,他摸了摸怀里的白面馒头,又摸了摸腰间的柴刀——柴刀还别在那里,刀身沾了泥,却依旧沉甸甸的。
路过老林入口时,他停下脚步,往林子里望了一眼。
夜色里的老林黑漆漆的,只能看到树影晃动,风穿过林子,发出“呜呜”的声音,像有人在哭。
可他却忽然想起白天听到的行商的话——那个剑脉残缺,最后却成为强者的剑修。
“剑脉残缺,也能练剑的……对吧?”
他小声对自己说,声音很轻,却带着一丝连自己都没察觉的倔强。
风卷着落叶吹过,他握紧了怀里的馒头,转身往家走。
就算现在不能学剑,就算每天只能劈柴,他也不想放弃——至少,他还能活着,还能等着那一点点可能的机会。
林澈挑着一担柴,慢慢往村里的杂货铺走。
这担柴有六十斤,比平时多了十斤——早上从剑馆回来后,他没歇气,在老林里多劈了一个时辰。
一是想多赚两个铜板,好早点攒够下次报名的学费;二是想让自己累一点,这样晚上躺在炕上的时候,就不会胡思乱想,不会再想起周铁山的轻蔑和学徒们的嘲笑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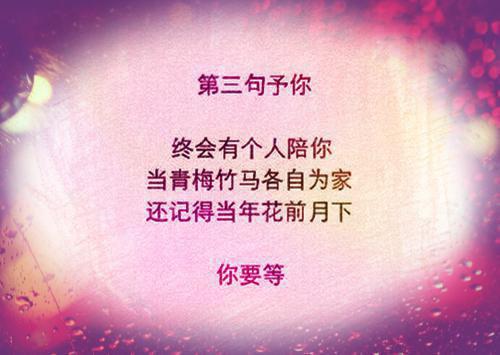
他在肩膀上垫了一块粗布,可六十斤的柴压上去,还是勒出一道深深的红印,从棉袄里透出来,疼得他每走一步都忍不住皱皱眉。
汗水浸湿了他的后背,棉袄里面的衣服都粘在了皮肤上,风一吹,凉得他打了个哆嗦,鸡皮疙瘩又起来了。
他走得很慢,每一步都很稳,眼睛盯着脚下的路,生怕柴捆掉下来——这担柴是他一下午的心血,劈的时候胳膊都抡酸了,要是掉了,不仅赚不到钱,还得重新劈,今晚就别想睡觉了。
走到村中间的巷口时,林澈停了下来,想歇口气。
巷口有一棵老槐树,树干得两三个人才能抱过来,虽然冬天里叶子都落光了,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桠,却依旧透着股老劲,枝桠在夕阳下投下长长的影子,像一条条黑色的带子铺在地上。
他把扁担从肩膀上卸下来,靠在槐树上,揉了揉肩膀——红印的地方一碰就疼,他只能轻轻按揉,缓解一下酸痛。
就在这时,一个嚣张的声音突然从巷子里传了过来:“哟,这不是想当剑修的劈柴小子吗?”
林澈抬头一看,只见三个少年从巷子里走了出来。
领头的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年,穿着一身宝蓝色的锦缎衣服,腰间挂着一块白玉佩,玉佩上刻着个“周”字,手里拿着一把新的木剑,剑身上还刻着精致的云纹——那是周铁山的侄子,周虎。
跟在周虎身后的两个少年,也是青岚剑馆的学徒,穿着统一的青色学徒服,手里也拿着木剑,脸上满是讨好的笑容,眼神却透着挑衅,像两条跟在主子身后的狗。
林澈不想惹麻烦,他低下头,把扁担往肩膀上扛,想绕开他们走。
可周虎却快步走过来,伸开胳膊拦住了他的去路,嘴角勾着一抹坏笑:“怎么?
看见我就想走?
早上不是还去我姑父的剑馆报名学剑吗?
怎么,被我姑父赶出来了?”
林澈没说话,侧身想从周虎旁边绕过去。
可周虎却突然伸出脚,狠狠踹在了他的柴捆上。
“哗啦!”
一声响,柴捆一下子倒在了地上,干柴滚落一地,有的滚到了巷口的路上,有的滚进了旁边的泥水里——中午的时候下过一场小雨,巷口有个低洼的地方,里面积满了泥水,黑乎乎的,还漂着点草屑。
“哎,你干什么!”
林澈忍不住喊了一声,声音里带着愤怒。
这担柴是他一下午劈的,现在撒了一地,有的柴还断了,怎么向王大叔交代?
怎么换今晚的饭吃?
“干什么?”
周虎冷笑一声,走过去,用脚踩住一根滚到他脚边的干柴,脚尖轻轻碾着,柴杆发出“咯吱、咯吱”的声音,像是要断了。
“我姑父没告诉你吗?
让你别再想学剑的事,好好劈你的柴。
你倒好,还敢往剑馆那边凑,我看你是不长记性!”
林澈看着那根被踩得变形的干柴,心里又疼又气。
他攥紧了拳头,指甲嵌进掌心,疼得他清醒了点——他不能动手,周虎是周铁山的侄子,要是打了他,周铁山肯定不会放过他,到时候别说劈柴赚钱了,能不能在落剑村待下去都难说。
他深吸一口气,压下心里的火气,蹲下身,开始捡地上的柴。
干柴散了一地,有的滚得很远,他得跑过去捡;有的掉进了泥水里,泥水没到了他的脚踝,冰冷刺骨,很快就把他的布鞋浸透了,冻得他腿发麻。
有一根柴滚到了水坑的最里面,他伸手去够,手指被水里的石头划破了,流出的血在泥水里很快就散开了,变成了淡淡的粉红色,可他没管,只是把柴捡起来,放在一边。
“捡啊,怎么不捡了?”
周虎站在旁边,抱着胳膊,笑着看着他,像在看一只被戏耍的猴子。
“是不是觉得累了?
早知道这样,就别痴心妄想学剑了,安安心心劈你的柴多好。
你看你现在,跟个泥猴似的,多丢人。”
跟在周虎身后的两个学徒也笑了起来,一个瘦高个的学徒说:“虎哥,你看他那样子,跟个乞丐似的,还想学剑,真是笑死人了。
我看他这辈子也就只能劈柴了。”
另一个矮胖的学徒也附和:“就是,剑脉残缺的废物,还想当剑修,我看他是脑子坏了。”
林澈没有理会他们的嘲笑,继续捡柴。
他把捡起来的柴一根根擦干净——没沾泥的就用袖子擦,沾了泥的就放在水坑边的石头上,用石头刮掉上面的泥,虽然刮不干净,至少能少带点水。
捡了快半个时辰,才把所有的柴都捡起来,堆成一小堆。
他找了根绳子,想重新把柴捆起来,可绳子刚才被柴压断了,断口处的纤维乱糟糟的,像被啃过的草,根本没法系紧。
林澈蹲在地上,指尖捏着那截断绳,心里有点慌——没有绳子,怎么把柴挑到杂货铺?
就在这时,他看到了自己的腰间——那里系着一根粗布腰带,是母亲生前给他缝的,灰扑扑的,边缘磨得起了毛,却异常结实,平时劈柴时勒着,能让他更用得上劲。
咬了咬牙,林澈解下腰带。
粗布贴着皮肤的地方还带着点体温,他把腰带铺在地上,先把没沾泥的干柴归拢到一起,码得整整齐齐,再小心翼翼地把泥水里的柴捡出来,用袖子擦去表面的泥,然后放在上面。
等柴都拢成一堆,他把腰带绕着柴堆缠了三圈,每一圈都用力勒紧,首到粗布嵌进柴缝里,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。
最后打了个死结,拽了拽,虽然柴堆看着歪歪扭扭,却总算能挑起来了。
“切,还挺能撑。”
周虎撇了撇嘴,觉得没趣了,“走了,跟个劈柴的耗着,浪费时间。”
说着,他带着两个学徒,晃悠悠地往剑馆方向走,路过林澈身边时,还故意撞了他一下。
林澈没站稳,差点摔在柴堆上,他扶住扁担,稳住身形,看着周虎的背影,眼底的火又冒了起来,却还是硬生生压了下去。
重新把扁担架到肩膀上时,林澈疼得倒吸一口凉气——刚才被周虎踹过的地方,此刻被扁担一压,像有块石头嵌在肉里,连带着胳膊都抬不太起。
他扶着扁担,站了好一会儿,才慢慢迈开步子。
柴堆有点松,走两步就晃一下,他只能走得极慢,时不时停下来,用手把滑出来的柴往里推。
夕阳渐渐沉到山后面,天边的橙红色被暗紫色取代,风也变凉了,吹得他耳朵发麻,脸上的泥水干了,紧绷绷的,像糊了层土。
路过村里的戏台时,几个村民还坐在那里聊天,看到他的样子,有人叹了口气,有人低声议论:“这孩子,又被周虎那小子欺负了吧?”
“唉,没爹没妈,又没剑脉,在村里难啊。”
林澈低着头,加快了脚步,不想听那些议论。
他知道村民们没有恶意,可那些话像细小的针,扎在他心上,比周虎的嘲笑更让他难受——他不想被人同情,更不想被人当成“可怜人”。
终于走到杂货铺时,天己经擦黑了。
杂货铺的木门虚掩着,里面透出昏黄的油灯光,王大叔正坐在柜台后面算账,算盘珠子打得“噼里啪啦”响,声音在安静的傍晚格外清晰。
听到脚步声,王大叔抬起头,看到林澈的样子,手里的算盘停了下来。
“小林?
你这是咋了?
浑身都是泥?”
王大叔连忙走出来,他五十多岁,头发花白,脸上满是皱纹,眼睛却很亮,说话总是慢声细语的。
看到林澈肩膀上的红印,还有手上的伤,他皱起眉头,“是不是周铁山的人又找你麻烦了?
是不是周虎那小子?”
林澈把柴挑到后院,卸下来时,腰带一松,两根柴滚了出来。
他连忙去捡,王大叔也蹲下来帮忙,捡起一根柴,摸了摸上面的泥,叹了口气:“肯定是周虎那混小子干的。
这孩子,仗着他姑父是馆主,整天在村里欺负人,早晚要吃亏。”
林澈蹲在地上,把柴摆整齐,声音有点闷:“王大叔,不怪他,是我自己不小心弄撒的。”
他不想让王大叔为难——王大叔的杂货铺要靠剑馆的学徒照顾生意,要是王大叔为了他去找周铁山理论,以后学徒们不来买东西,王大叔的生意肯定不好做。
王大叔没再追问,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,力道很轻,怕碰疼他:“傻孩子,别总自己扛着。
这天越来越冷,柴不好劈,要是累了,就歇一天,别硬撑。”
说着,他转身回了屋,很快拿了一个白面馒头出来,递到林澈手里。
馒头还带着点温乎气,捏在手里软软的。
“今天柴挑得多,这个给你,比黑面的软和,填肚子。”
林澈愣住了。
白面馒头是王大叔自己都舍不得吃的,平时只有逢年过节,或者他孙子来看他的时候,才会蒸几个。
“王大叔,我不能要,我有黑面馒头。”
他把馒头往回推,怀里还揣着中午剩下的那个黑面馒头,硬邦邦的,硌得胸口有点疼。
“拿着!”
王大叔把馒头塞到他手里,语气很坚决,“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,总吃硬馒头不行,会把胃吃坏的。
对了,前几天你说想去剑馆,怎么样了?
成了吗?”
提到剑馆,林澈握着馒头的手紧了紧,指尖有点发凉。
他摇了摇头,声音更低了:“没成,周馆主说我剑脉残缺,引不动剑元,不收我。”
王大叔哦了一声,沉默了片刻,然后拍了拍他的后背,像拍自己的孙子一样:“没事,咱不学剑也能过日子。
你手巧,劈柴又勤快,以后要是想做点别的,比如跟着张铁匠学打铁,或者跟着我看铺子,大叔都能帮你琢磨琢磨。”
林澈点了点头,没说话。
他攥着温乎的馒头,心里暖暖的,眼眶却有点发热。
他知道王大叔是为他好,可“学剑”这两个字,像颗种子,早就埋在了他心里,就算现在没发芽,也没彻底死掉。
“王大叔,我先走了,明天再来劈柴。”
林澈把馒头揣进怀里,又接过王大叔递来的两个铜板——这是今天的工钱,比平时多了一个,他知道是王大叔特意多给的。
“路上慢点,天黑了,小心脚下。”
王大叔站在门口,看着他的背影,还在叮嘱,“要是怕黑,就喊一声,大叔给你拿个灯笼。”
“不用了王大叔,我能走。”
林澈应了一声,挑着空扁担往家走。
他家在村西的角落里,是一间破旧的土坯房,屋顶漏了好几处,去年冬天还塌过一次,是王大叔请人帮他修好的。
走在路上,他摸了摸怀里的白面馒头,又摸了摸腰间的柴刀——柴刀还别在那里,刀身沾了泥,却依旧沉甸甸的。
路过老林入口时,他停下脚步,往林子里望了一眼。
夜色里的老林黑漆漆的,只能看到树影晃动,风穿过林子,发出“呜呜”的声音,像有人在哭。
可他却忽然想起白天听到的行商的话——那个剑脉残缺,最后却成为强者的剑修。
“剑脉残缺,也能练剑的……对吧?”
他小声对自己说,声音很轻,却带着一丝连自己都没察觉的倔强。
风卷着落叶吹过,他握紧了怀里的馒头,转身往家走。
就算现在不能学剑,就算每天只能劈柴,他也不想放弃——至少,他还能活着,还能等着那一点点可能的机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