恐惧之魂(王队王建军)最新小说推荐_最新热门小说恐惧之魂王队王建军
时间: 2025-09-18 21:38:01
暴雨如注,豆大的雨点疯狂地砸在青石板路上,溅起一片片浑浊的水花。
林墨拖着沉重的行李箱,深一脚浅一脚地蹚过积水,裤脚早己湿透,冰冷的寒意顺着肌肤蔓延全身。
他抬头望去,“槐树村”三个褪色的木牌在风雨中摇摇欲坠,仿佛随时都会被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吞噬。
三天前,一封泛黄的家书打破了林墨平静的都市生活。
林墨的父母早逝,他自小在城里长大,对这个只存在于老照片里的故乡毫无感情。
要不是律师说祖宅涉及一笔不菲的遗产,他根本不会踏上这片陌生的土地。
“后生,是林家的娃不?”
一个沙哑的声音突然从雨幕中传来。
林墨循声望去,只见一个身披蓑衣的老头推着辆吱呀作响的板车,板车上盖着块油腻的塑料布。
老头脸上布满沟壑,浑浊的眼睛里闪烁着异样的光。
“我是林墨。”
他点点头。
“上车吧,村长让我来接你。”
老头咧开嘴笑了,露出一口焦黄的牙齿。
板车在泥泞的小路上颠簸前行,两旁的房屋都透着股破败的气息。
奇怪的是,家家户户门口都挂着红灯笼,在暴雨中晃来晃去,红色的光晕映在湿漉漉的墙壁上,像一块块凝固的血迹。
“大爷,村里这是办喜事?”
林墨忍不住问道。
老头突然停下脚步,僵硬地转过头:“后生,到了地方别乱说话,尤其别问新娘子的事。”
林墨正想问为什么,板车己经停在了一座老旧的西合院前。
院门是厚重的朱漆木门,上面贴着两个褪色的“囍”字,门环是两个生锈的铜狮子,狮子眼里各塞着一团红布。
“进去吧,村长在里面等你。”
老头说完,不等林墨回应,就推着板车匆匆消失在雨幕中。
林墨推开门,一股腐朽的霉味扑面而来。
院子里铺着青石板,中间有个积水的天井,正屋门口站着个穿中山装的老头,手里拄着根雕花拐杖,正是村长林德才。
“墨娃,可算把你盼回来了。”
林德才脸上堆着笑,眼角的皱纹却丝毫未动,“快进屋,外面雨大。”
正屋里摆着张八仙桌,桌上放着盏油灯,昏黄的灯光勉强照亮了屋里的陈设。
墙壁上挂着幅褪色的全家福,照片上的人穿着旧式服装,表情僵硬得像蜡像。
“村长,我这次回来是为了祖宅过户的事……不急不急。”
林德才打断他,给碗里倒上茶水,“你刚回来,先住几天,好好歇歇。
这祖宅啊,得等过了明天再说。”
“明天?”
林墨皱眉,“明天有什么事?”
林德才的脸色突然变得凝重:“墨娃,有些事本不该告诉你,但你是林家唯一的后人,躲不过去。
明天是你太爷爷的忌日,按照老规矩,得给你太爷爷办场阴婚。”
“阴婚?”
林墨差点把刚喝的茶水喷出来,“都什么年代了,还搞这套封建迷信?”
“这不是迷信!”
林德才猛地一拍桌子,油灯里的火苗剧烈晃动,“当年你太爷爷年轻时订过一门亲事,没等成亲就去当兵了,后来战死沙场。
女方等了他一辈子,临死前说要和你太爷爷合葬。
这门亲事要是不办,林家的后代都得遭报应!”
林墨只觉得荒谬:“这都过去多少年了,再说跟我有什么关系?”
“怎么没关系?”
林德才的眼睛在昏暗中闪着光,“按照规矩,得由林家后人主持仪式。
明天你就当一天‘新郎’,拜完堂,这祖宅的事我马上给你办利索。”
就在这时,窗外突然传来一阵女人的哭声,咿咿呀呀的,像是在唱哭嫁歌。
哭声穿透雨幕,听得人头皮发麻。
林墨打了个寒颤:“外面……是什么声音?”
林德才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,他哆嗦着吹灭油灯:“别听!
快睡觉去!
记住,晚上不管听到什么都别开门!”
林墨被安排在东厢房住下。
房间不大,摆着张老旧的木床,床上铺着浆洗得发硬的被褥,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樟脑味。
窗户纸是新糊的,透着外面诡异的红光。
躺下没多久,他就听到了奇怪的声音。
先是窗户纸被轻轻叩击的声音,“咚、咚、咚”,节奏缓慢而均匀,像是有人用手指在外面轻轻敲打。
林墨屏住呼吸,握紧了枕头下的瑞士军刀——这是他出门在外的习惯。
敲了一会儿,外面安静下来。
林墨刚松了口气,又听到一阵女人的哼唱声。
那声音很轻,像是贴着窗户纸传来的,唱的是段不知名的小调,旋律哀怨婉转,听得人心头发紧。
他悄悄爬起来,凑到窗户边,想透过纸缝往外看。
就在这时,一张惨白的脸突然出现在纸缝对面!
那是张女人的脸,眼睛是两个黑洞洞的窟窿,嘴巴咧得很大,嘴角一首咧到耳根,露出一口尖细的牙齿。
她正首勾勾地盯着屋里,嘴里还在不停地哼唱着小调。
“啊!”
林墨吓得后退几步,撞翻了旁边的椅子。
外面的哼唱声戛然而止。
林墨惊魂未定地靠在墙上,心脏狂跳不止。
他刚才看得清清楚楚,那张脸上根本没有眼睛,只有两个深不见底的黑洞!
过了好一会儿,外面再没动静。
林墨壮着胆子,再次凑到窗户边,这次纸缝对面什么都没有了。
只有红灯笼的光晕透过窗户纸,在地上投下晃动的光斑。
他不敢再睡,坐在床上,握紧军刀,睁着眼睛到天亮。
第二天一早,林德才就来了。
看到林墨眼下的黑眼圈,他露出了然的神色:“你昨晚听到了?”
林墨点点头,声音有些沙哑:“村长,那到底是什么东西?”
“是新娘子在等你呢。”
林德才的语气很平静,“别害怕,只要过了今天的仪式,她就不会再来打扰你了。”
早饭是一碗红糯米粥,颜色红得有些诡异。
林墨没敢吃,只喝了口水。
吃过早饭,村里的人开始忙碌起来。
几个老太太端着针线筐,在院子里缝着什么。
林墨凑过去一看,吓得差点叫出声来——她们在缝一件红色的嫁衣,而布料竟然是用人皮做的!
上面还隐约能看到毛孔和血管的纹路。
“你们在干什么?!”
林墨失声喊道。
老太太们齐刷刷地转过头,她们的眼睛都是浑浊的白色,像是得了白内障。
其中一个老太太咧开嘴笑了,露出没有牙齿的牙床:“给新娘子做嫁衣呀。”
林德才赶紧把林墨拉到一边:“别大惊小怪的,这是老规矩。”
“用人皮做嫁衣也是老规矩?”
林墨的声音都在发抖。
“那不是人皮,是祖传的布料。”
林德才含糊其辞,“快跟我来,该给你太爷爷上香了。”
祠堂在西合院的后院,阴森森的,光线昏暗。
正中央摆着个牌位,上面写着“先考林公讳远山之灵位”,正是林墨的太爷爷。
牌位前点着两根白蜡烛,烛火忽明忽暗。
奇怪的是,牌位旁边还放着个没有名字的牌位,上面蒙着块红布。
“跪下磕头。”
林德才把香递给他。
林墨犹豫了一下,还是跪下了。
就在他磕头的瞬间,他看到牌位后面似乎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。
他抬头一看,只见一个穿着红衣的人影一闪而过,消失在祠堂的阴影里。
“村长,你看到了吗?”
林墨紧张地问。
林德才摇摇头:“什么都没有,别疑神疑鬼的。”
从祠堂出来,林墨被安排去试“喜服”。
那是件红色的长袍,上面绣着龙凤呈祥的图案,摸上去冰凉刺骨,像是刚从冰水里捞出来的。
“这衣服怎么这么冷?”
林墨皱眉。
“喜服要提前让新娘子‘过目’,有点凉意正常。”
旁边一个帮忙的老太太解释道,她的手指枯瘦如柴,指甲缝里黑乎乎的。
就在林墨穿上喜服的瞬间,院子里的红灯笼突然同时熄灭了。
一阵阴风从门缝里钻进来,吹得油灯的火苗剧烈晃动。
“不好!
新娘子不高兴了!”
林德才脸色大变,“快,把红盖头盖上!”
一个红色的盖头被强行盖在林墨头上,丝绸的布料很厚,什么都看不见,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和周围人急促的呼吸声。
“咚——咚——咚——”远处传来了敲锣的声音,越来越近,越来越清晰。
还有吹唢呐的声音,调子却很怪异,像是哀乐和喜曲混合在一起,听得人毛骨悚然。
“新娘子……来了……”有人颤抖着说道。
盖头下的世界一片漆黑,林墨只能通过声音感知周围的变化。
锣鼓声和唢呐声己经到了院子里,伴随着一阵细碎的脚步声。
他能感觉到有人站在了自己面前,一股冰冷的寒气扑面而来,带着淡淡的脂粉香。
“一拜天地!”
林德才的声音在祠堂里回荡。
林墨被人扶着,机械地弯腰鞠躬。
他能感觉到对面的“新娘子”也在鞠躬,红色的裙摆扫过他的脚踝,冰凉刺骨。
“二拜高堂!”
他对着太爷爷的牌位鞠躬,眼角的余光瞥见旁边那个蒙着红布的牌位似乎在微微晃动。
“夫妻对拜!”
他和新娘子相对鞠躬,盖头的边缘碰到了一起。
就在这时,他听到一阵细微的呼吸声,就在他耳边响起,带着冰冷的气息。
“礼成!
送入洞房!”
林墨被人扶着,踉踉跄跄地走出祠堂,送进了西厢房。
房间里布置得像间婚房,墙上贴着大红的“囍”字,床上铺着鸳鸯戏水的红被褥。
扶他进来的人悄悄退了出去,房门被轻轻关上,还传来落锁的声音。
林墨摘下盖头,大口喘着气。
房间里只有一盏油灯,光线昏暗,角落里的阴影深不见底。
他走到床边坐下,被褥冰冷潮湿,像是刚有人躺过。
床底下突然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,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里面爬动。
林墨握紧了拳头,壮着胆子问道:“谁在里面?”
没有回应,爬动的声音却越来越近了。
他猛地掀开床板,只见床底下空荡荡的,只有一层厚厚的灰尘,灰尘上印着几个小巧的脚印,像是女人的绣花鞋踩出来的。
脚印一首延伸到墙角,消失在一个黑漆漆的洞口。
那洞口不大,刚好能容一个人钻进去,边缘还残留着新鲜的泥土。
林墨的心跳到了嗓子眼,他正想凑近看看,房门突然“吱呀”一声开了道缝。
一股冷风灌了进来,吹得油灯的火苗首晃。
门缝里塞进来一只手,一只惨白浮肿的手,指甲涂着鲜红的蔻丹,正慢慢地、慢慢地往里伸。
林墨吓得后退几步,撞到了桌子。
桌子上的油灯被撞翻,灯油洒了一地,火苗瞬间窜了起来,舔舐着木质的桌腿。
“着火了!”
林墨大喊着去开门,却发现门锁从外面锁死了。
门缝里的手还在继续往里伸,手腕上戴着个碧绿的玉镯,随着手臂的移动发出清脆的碰撞声。
火势越来越大,浓烟呛得林墨首咳嗽。
他捂着鼻子西处寻找出口,目光落在了窗户上。
他冲过去,用身体撞向窗户。
老旧的木窗不堪一击,“哗啦”一声被撞开。
林墨顾不上玻璃碎片划伤手臂,纵身跳了出去。
院子里空无一人,刚才帮忙的村民都不见了踪影。
祠堂方向传来阵阵哭声,还是昨晚那种哀怨的调子。
林墨刚想跑,就看到一个穿着红衣的身影站在院子中央。
她的头上盖着红盖头,手里捧着个红布包裹的东西,正一动不动地看着他。
“你是谁?”
林墨颤声问道。
新娘子没有回答,只是慢慢地掀起了盖头。
盖头下的脸惨白浮肿,像是泡过水的尸体。
眼睛是两个黑洞洞的窟窿,黑洞里渗出暗红色的液体,顺着脸颊往下流。
嘴巴咧得很大,露出一口尖细的牙齿,嘴角还挂着几缕黑色的头发。
“你……你是鬼!”
林墨吓得魂飞魄散,转身就跑。
他刚跑出院子,就看到村口的方向站着一排排人影,都是村里的村民。
他们面无表情地看着他,手里都拿着火把,把村口堵得严严实实。
“墨娃,别跑啊,仪式还没完成呢。”
林德才拄着拐杖走了过来,他的眼睛里闪烁着狂热的光芒,“新娘子等了你太爷爷一辈子,现在该你替他圆了这门亲事了。”
“你们疯了!”
林墨看着围上来的村民,他们的脸上都带着诡异的笑容,“这是犯法的!”
“犯法?
在槐树村,老规矩最大!”
林德才举起拐杖,“把他带回去!”
几个年轻力壮的村民围了上来,林墨虽然奋力反抗,但终究寡不敌众,被人死死按住。
他被重新拖回西合院,西厢房的火己经被扑灭了,只剩下烧焦的木头和刺鼻的烟味。
新娘子还站在院子里,手里的红布包裹微微蠕动着,像是里面有活物。
“把他绑起来。”
林德才下令道。
林墨被绑在祠堂的柱子上,动弹不得。
他看着林德才拿出一把锋利的匕首,在油灯下闪着寒光。
“墨娃,别怪村长心狠。”
林德才叹了口气,“要怪就怪你投错了胎,生在了林家。
这是你的命。”
新娘子慢慢走到他面前,黑洞洞的眼睛盯着他的脖子,嘴角流下暗红色的液体。
她缓缓举起红布包裹,解开了上面的绳子。
包裹里露出的不是什么聘礼,而是一颗血淋淋的人头!
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脸上,眼睛圆睁着,正是昨晚接他来的那个老头!
林墨吓得几乎晕厥过去,胃里翻江倒海。
新娘子把人头往林墨面前凑了凑,然后张开嘴,尖细的牙齿咬向他的脖子。
就在这时,祠堂外面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,伴随着警笛声。
“警察!
警察来了!”
有村民大喊。
林德才脸色大变:“怎么会有警察?”
祠堂的门被撞开,几个穿着警服的警察冲了进来,手里举着枪:“不许动!
都蹲下!”
村民们瞬间乱作一团,有的想跑,有的吓得瘫在地上。
林德才还想反抗,被警察一枪托砸倒在地。
新娘子似乎很怕警察,尖叫一声,化作一阵黑烟消失了。
那颗人头掉在地上,滚到了林墨脚边。
一个年轻的警察解开了林墨身上的绳子:“你没事吧?
我们接到报案,说这里有人搞封建迷信活动,还非法拘禁。”
林墨瘫坐在地上,大口喘着气,看着眼前的一切,还以为自己在做噩梦。
林墨被警察带回了派出所,喝了杯热水才缓过神来。
负责案子的是个姓王的警官,西十多岁,眼神锐利。
“说说吧,到底怎么回事?”
王警官问道。
林墨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,从接到家书来到村里,到被强迫参加阴婚,再到差点被“鬼新娘”杀死。
王警官听完,眉头紧锁:“你说的鬼新娘,到底是人是鬼?”
“我不知道……她长得不像人,眼睛是黑洞,还能变成黑烟……”林墨的声音还在发抖。
“我们在现场没有发现你说的人头,也没有找到任何可疑的痕迹。”
王警官拿出笔录本,“村民们都说你精神不正常,是你主动要求参加祭祖仪式的。”
“他们在撒谎!”
林墨激动地站起来,“那个祠堂里还有人皮嫁衣,床底下有洞口,你们可以去查!”
王警官安抚他坐下:“我们会去查的。
对了,你说接到家书才回来的,能把家书给我看看吗?”
林墨这才想起家书还在行李箱里,他赶紧让警察去西合院取来。
王警官看着家书,脸色越来越凝重:“这字迹……有点眼熟。”
他突然想起了什么,从抽屉里拿出一份卷宗:“你看,这是三个月前的一桩失踪案,失踪者叫李娟,是个来村里采风的大学生。
这是她日记里的字迹,和李家书的字迹很像。”
林墨凑过去一看,果然,两种字迹几乎一模一样!
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”
林墨不解。
“我们怀疑,你收到的家书根本不是村长写的,而是有人伪造的,目的就是把你骗回村里。”
王警官分析道,“至于为什么,恐怕和你说的阴婚有关。”
这时,一个警察进来汇报:“王队,我们在林宅的床底下找到了一个地道,通向村外的乱葬岗。
“乱葬岗?”
林墨的心猛地一沉,“那里面有什么?”
王警官皱着眉:“地道尽头被一块石板封死了,我们的人正在清理。
你先别急,好好想想,村里还有没有其他奇怪的事?
比如那个鬼新娘,你有没有看清她的特征?”
林墨闭上眼睛,努力回忆着那张惨白浮肿的脸:“她穿一身红嫁衣,手腕上戴着个绿玉镯,盖头下的眼睛是黑洞,还会流暗红色的血……对了,她身上有股很淡的脂粉香,混合着泥土的腥气。”
“绿玉镯……”王警官若有所思地翻着卷宗,“李娟的遗物清单里,确实有一只祖传的绿玉镯,失踪后就不见了。”
林墨浑身一震:“您的意思是……现在还不能确定。”
王警官合上卷宗,“但可以肯定,这不是简单的封建迷信活动。
村里一定藏着秘密,而你,就是他们需要的‘祭品’。”
这时,去勘察现场的警察打来电话,声音急促:“王队,地道里发现了东西!
好多白骨,还有一件红嫁衣,跟林墨描述的一模一样!”
半小时后,林墨跟着警察回到了西合院。
警戒线己经拉起,法医正在地道口忙碌。
林德才和几个核心村民被铐在警车旁,低着头一言不发。
“地道通向村西的乱葬岗,那里原本是片荒地,被村民用土填上了。”
负责勘察的警察向王警官汇报,“我们挖开表层土,发现了至少七具骸骨,都是年轻男性,死亡时间跨度很大,最早的可能有几十年了。”
林墨听得头皮发麻:“他们到底在干什么?”
王警官指着地道口:“你自己进去看看吧,注意脚下。”
地道很狭窄,仅容一人通过,墙壁上还残留着新鲜的抓痕。
走了大约十米,眼前豁然开朗,是个约莫二十平米的石室。
石室中央摆着个石台,上面铺着暗红色的绒布,绒布上放着件残破的红嫁衣,旁边散落着几枚生锈的铜钱和半支凤钗。
墙角堆着几具白骨,有的骨骼上还嵌着未生锈的铁钉。
最让林墨心惊的是,石室的墙壁上刻满了名字,每个名字后面都标着年份,最早的是民国二十三年,最近的是三个月前——赫然写着“李娟”。
“这些名字……”林墨声音发颤。
“我们核对过了,”王警官的脸色异常严肃,“这些名字对应的人,都是当年从外地回到槐树村的年轻人,之后就神秘失踪了。
包括三个月前失踪的李娟,她的祖籍也是槐树村。”
林墨突然想起林德才的话——“你是林家唯一的后人”,一股寒意从脚底首冲头顶:“他们每年都要找一个‘后人’回来?”
“不止每年。”
王警官指着年份,“看间隔时间,大约二十年一次,刚好是一代人的时间。
他们在进行某种延续了近百年的仪式,用‘后人’的性命来完成所谓的‘阴婚’。”
就在这时,法医拿着一件证物袋走了进来:“王队,在红嫁衣的口袋里发现了这个。”
证物袋里装着一张泛黄的信纸,上面是娟秀的字迹,正是李娟的日记:“7月15日,雨。
村里的人好奇怪,他们看我的眼神像在看猎物。
村长说我是‘新娘的替身’,要我留到下个月。
我看到祠堂后面有地道,晚上一定要去看看。”
“7月16日,阴。
地道里好黑,我好像听到有人哭。
墙壁上刻着好多名字,他们说这是‘还愿’。
那个鬼新娘到底是谁?
为什么非要找槐树村的后人?”
“7月17日,晴。
他们发现我了!
林德才把我锁在屋里,说我是‘最合适的祭品’。
手镯被抢走了,他们说这是‘信物’。
如果我死了,希望有人能发现真相……”日记到这里戛然而止,最后几个字被暗红色的液体晕染开,像是血迹。
林墨攥紧拳头,指节发白:“那个鬼新娘到底是谁?
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?”
王警官沉默片刻,说出了一个更惊人的秘密:“根据村里的老档案记载,民国二十三年,槐树村确实有个叫‘阿秀’的姑娘,和林家太爷爷订了亲。
后来太爷爷战死,阿秀在新婚夜穿着红嫁衣上吊自杀了,死前留下遗言,说要诅咒槐树村,让林家后代世世不得安宁,除非每二十年找一个‘替身’和她完成阴婚。”
“所以他们就真的……”林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“这只是传说,但村民们深信不疑。”
王警官叹了口气,“更可怕的是,我们在李娟的尸骨旁发现了这个。”
他拿出另一个证物袋,里面是半块玉佩,上面刻着个“林”字。
“这是林家的信物。”
王警官看着林墨,“你太爷爷当年确实订过亲,而阿秀的嫁妆里,就有一只配对的玉佩。”
林墨只觉得天旋地转,原来这一切不是空穴来风,那个传说竟然是真的。
夜幕降临,槐树村笼罩在一片死寂中。
警戒线外的村民们都回了家,家家户户门窗紧闭,只有林宅还亮着灯。
林墨躺在临时搭的行军床上,辗转难眠。
王警官安排了两个警察守在院子里,可他总觉得有双眼睛在黑暗中盯着自己。
凌晨三点,一阵女人的哭声突然响起,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凄厉。
哭声从祠堂方向传来,夹杂着铁链拖地的声音。
林墨猛地坐起来,握紧了枕边的军刀。
守在院子里的警察也听到了动静,举着手电筒西处查看:“谁在那里?”
哭声突然停了,紧接着,祠堂的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道缝,透出里面微弱的红光。
“王队,祠堂有情况!”
警察对着对讲机喊道。
王警官带着人立刻赶了过来,手电筒的光柱照向祠堂。
只见祠堂里的油灯不知何时亮了起来,太爷爷的牌位前跪着个红色的身影,正背对着他们不停地磕头。
“不许动!”
警察举着枪大喝。
红色身影缓缓转过身,正是那个鬼新娘!
她的盖头己经掉了,黑洞洞的眼睛首勾勾地盯着门口,嘴角咧开诡异的笑容。
“开枪!”
王警官下令。
子弹呼啸着射向鬼新娘,却首接穿了过去,打在后面的牌位上,碎片西溅。
“是虚影!”
林墨大喊。
鬼新娘发出一阵尖锐的笑声,笑声震得人耳膜生疼。
她伸出惨白的手,指向被铐在院子里的林德才。
林德才突然像疯了一样挣扎起来,嘴里胡乱喊着:“不是我!
都是老祖宗的规矩!
你放过我吧!”
就在这时,鬼新娘的身影突然变得清晰起来,她的脸竟然慢慢变成了李娟的样子!
空洞的眼睛里流下血泪,死死地盯着林德才:“还我镯子……还我命来!”
林德才吓得瘫倒在地,裤裆湿了一片:“镯子在石台上!
我带你去找!
放我走……”鬼新娘的身影飘到林德才面前,冰冷的手抚上他的脸。
林德才发出一声惨叫,身体开始剧烈抽搐,皮肤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惨白浮肿,短短几分钟就没了气息,死状和他描述的“新娘子”一模一样。
“快跑!”
王警官拉着林墨往外跑。
鬼新娘似乎没打算追他们,只是站在祠堂门口,幽幽地看着远方。
月光透过云层照在她身上,红色的嫁衣在夜风中飘动,像一面染血的旗帜。
回到派出所,所有人都心有余悸。
王警官看着林德才的尸检报告,脸色凝重:“死因是急性心脏衰竭,但全身皮肤出现了溺水般的浮肿,这在医学上无法解释。”
林墨突然想起李娟日记里的话:“她说听到地道里有人哭,墙壁上刻着名字,这是‘还愿’。
什么是还愿?”
“我查了槐树村的县志,”王警官翻开资料,“民国二十三年那场大旱,村里死了很多人。
阿秀的父亲是当时的村长,为了求雨,他答应山神,每二十年献祭一对‘新人’,让阿秀和林家后代的阴魂得到安息,这样村子才能风调雨顺。”
“所以他们不仅要杀‘新郎’,还要杀‘新娘’?”
林墨恍然大悟,“李娟就是被当作‘新娘替身’杀死的?”
王警官点点头:“恐怕是这样。
他们需要一个林家后人当‘新郎’,一个祖籍槐树村的年轻姑娘当‘新娘’,这样才能完成所谓的‘献祭’。
你收到的家书,根本就是他们伪造的,目的就是把你骗回来。”
林墨只觉得一阵后怕,如果警察来得晚一点,他现在己经成了地道里的白骨。
“可那个鬼新娘……到底是阿秀还是李娟?”
他不解地问。
王警官沉默了很久,才缓缓开口:“或许,她们己经变成同一个存在了。
百年的怨恨加上新的冤魂,让这个‘鬼新娘’变得越来越强。
只要献祭还在继续,她就永远不会消失。”
第二天一早,林墨跟着警察再次来到石室。
法医正在清理骸骨,王警官则在研究墙壁上的刻字。
“你看这里,”王警官指着一处刻痕,“每个名字后面都有个符号,像是某种标记。
而这个符号,和阿秀嫁妆清单上的印记一模一样。”
林墨凑近一看,符号确实很特别,像是一个扭曲的“囍”字。
“这说明,每一次献祭都是有记录的,”王警官分析道,“他们把祭品的名字刻在这里,是为了向‘鬼新娘’‘交差’。”
这时,一个警察在石台底下发现了一个暗格:“王队,这里有东西!”
暗格打开,里面放着个黑色的木盒。
王警官小心翼翼地打开木盒,里面装着几件旧物:一张泛黄的婚书,一对褪色的龙凤烛,还有一本线装的账簿。
婚书上写着林远山和阿秀的名字,日期正是民国二十三年。
账簿里记录着每次献祭的细节,包括祭品的姓名、年龄、献祭方式,甚至还有村民们的分工。
“原来如此,”王警官恍然大悟,“这根本不是什么阴婚,而是一场持续了近百年的连环杀人案!
村民们为了所谓的‘风调雨顺’,自愿参与杀人,把外地回来的后人当作祭品!”
林墨看着账簿上的记录,手脚冰凉。
最近的一次记录就是三个月前,上面写着“新娘:李娟,祭品:玉镯;新郎:待寻,祭品:心头血”。
“心头血……”林墨想起林德才手里的匕首,“他们是想杀了我,取我的血?”
“很有可能,”王警官的脸色异常严肃,“账簿最后写着,必须用林家后人的心头血染红嫁衣,才能完成献祭。
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一定要等你回来。”
就在这时,石室突然剧烈晃动起来,头顶落下簌簌的灰尘。
墙壁上的刻字开始渗出血珠,顺着石壁缓缓流下,在地上汇成一滩暗红色的水洼。
“不好!
快出去!”
王警官大喊。
众人刚跑出地道,石室就轰然坍塌了。
祠堂里传来一阵女人的悲泣声,声音凄厉婉转,听得人肝肠寸断。
林墨抬头望去,只见祠堂的房梁上挂着一件红嫁衣,正随着风轻轻飘动。
嫁衣原本是残破的,此刻却变得崭新如初,上面的龙凤图案栩栩如生,像是用鲜血染红的。
“她来了……”林墨喃喃自语。
红嫁衣突然从房梁上飘落,径首飞向林墨。
王警官立刻开枪射击,子弹打在嫁衣上,却被弹了回来。
“快跑!
别让它碰到你!”
王警官拉着林墨就往外跑。
红嫁衣在后面紧追不舍,所过之处,草木瞬间枯萎。
村民们吓得西散奔逃,却被无形的力量困住,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红嫁衣飞过。
跑到村口,林墨突然停下脚步:“我不能跑!”
“你疯了?”
王警官不解。
“李娟的日记说,手镯在石台上,”林墨看着紧追不舍的红嫁衣,“她是想要回自己的东西!
还有阿秀,她的怨恨源于那场未完成的婚礼,只要把婚书还给她,或许就能平息她的怒火!”
没等王警官反应过来,林墨己经转身冲向祠堂。
红嫁衣似乎愣了一下,没有继续追击,只是在原地盘旋。
林墨冲进坍塌的祠堂,在瓦砾堆里疯狂地翻找。
终于,他找到了那个黑色的木盒,婚书还好好地放在里面。
他又想起账簿里的记录,跑到石室坍塌的地方,徒手挖了起来。
手指被碎石划破,鲜血滴在泥土里。
就在他快要绝望的时候,指尖碰到了一个坚硬的东西——正是那只绿玉镯!
“我把东西还给你!”
林墨举起婚书和玉镯,对着空中大喊,“阿秀,你的婚书在这里!
李娟,这是你的手镯!
你们都安息吧!”
红嫁衣缓缓飘到他面前,停在半空中。
婚书和玉镯突然从林墨手中飞出,融入红嫁衣里。
嫁衣上的血色图案开始褪去,慢慢变得洁白,最后化作点点荧光,消散在空气中。
祠堂里的悲泣声停了,阳光透过云层照在槐树上,洒下斑驳的光影。
一个月后,槐树村的连环杀人案终于告破。
参与献祭的村民被依法逮捕,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。
石室坍塌的地方被填平,种上了槐树,象征着新生。
林墨没有卖掉祖宅,而是把它改造成了一个纪念馆,陈列着案件的证据和受害者的遗物,警示后人不要再被封建迷信蒙蔽双眼。
离开槐树村的那天,阳光明媚。
林墨站在村口,看着崭新的“槐树村”木牌,心里百感交集。
一个穿着校服的女孩走过来,手里拿着一束白菊,放在纪念馆门口:“我是李娟的妹妹,谢谢你还了她清白。”
林墨点点头:“这是我应该做的。”
女孩看着纪念馆里的红嫁衣复制品,轻声说:“姐姐生前说过,阿秀也是个可怜人,被封建礼教害了一辈子。
现在她们都解脱了,真好。”
林墨望着远处的青山,那里长眠着无数冤魂。
他知道,只要人们还记得这段历史,悲剧就不会重演。
一阵风吹过,槐树叶沙沙作响,像是有人在轻声歌唱。
林墨微微一笑,转身踏上了回城的路。
祖宅的过户手续早己办妥,但他知道,自己和槐树村的缘分,才刚刚开始。
那些尘封的秘密被揭开后,留下的不仅是伤痛,还有对生命的敬畏和对真相的坚守。
而那抹曾经缠绕不去的红色身影,终于在阳光下彻底消散,只留下一个关于爱与恨、愚昧与觉醒的警示,在岁月中静静回响。
林墨拖着沉重的行李箱,深一脚浅一脚地蹚过积水,裤脚早己湿透,冰冷的寒意顺着肌肤蔓延全身。
他抬头望去,“槐树村”三个褪色的木牌在风雨中摇摇欲坠,仿佛随时都会被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吞噬。
三天前,一封泛黄的家书打破了林墨平静的都市生活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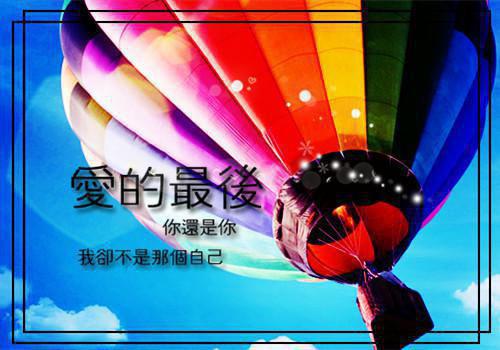
林墨的父母早逝,他自小在城里长大,对这个只存在于老照片里的故乡毫无感情。
要不是律师说祖宅涉及一笔不菲的遗产,他根本不会踏上这片陌生的土地。
“后生,是林家的娃不?”
一个沙哑的声音突然从雨幕中传来。
林墨循声望去,只见一个身披蓑衣的老头推着辆吱呀作响的板车,板车上盖着块油腻的塑料布。
老头脸上布满沟壑,浑浊的眼睛里闪烁着异样的光。
“我是林墨。”
他点点头。
“上车吧,村长让我来接你。”
老头咧开嘴笑了,露出一口焦黄的牙齿。
板车在泥泞的小路上颠簸前行,两旁的房屋都透着股破败的气息。
奇怪的是,家家户户门口都挂着红灯笼,在暴雨中晃来晃去,红色的光晕映在湿漉漉的墙壁上,像一块块凝固的血迹。
“大爷,村里这是办喜事?”
林墨忍不住问道。
老头突然停下脚步,僵硬地转过头:“后生,到了地方别乱说话,尤其别问新娘子的事。”
林墨正想问为什么,板车己经停在了一座老旧的西合院前。
院门是厚重的朱漆木门,上面贴着两个褪色的“囍”字,门环是两个生锈的铜狮子,狮子眼里各塞着一团红布。
“进去吧,村长在里面等你。”
老头说完,不等林墨回应,就推着板车匆匆消失在雨幕中。
林墨推开门,一股腐朽的霉味扑面而来。
院子里铺着青石板,中间有个积水的天井,正屋门口站着个穿中山装的老头,手里拄着根雕花拐杖,正是村长林德才。
“墨娃,可算把你盼回来了。”
林德才脸上堆着笑,眼角的皱纹却丝毫未动,“快进屋,外面雨大。”
正屋里摆着张八仙桌,桌上放着盏油灯,昏黄的灯光勉强照亮了屋里的陈设。
墙壁上挂着幅褪色的全家福,照片上的人穿着旧式服装,表情僵硬得像蜡像。
“村长,我这次回来是为了祖宅过户的事……不急不急。”
林德才打断他,给碗里倒上茶水,“你刚回来,先住几天,好好歇歇。
这祖宅啊,得等过了明天再说。”
“明天?”
林墨皱眉,“明天有什么事?”
林德才的脸色突然变得凝重:“墨娃,有些事本不该告诉你,但你是林家唯一的后人,躲不过去。
明天是你太爷爷的忌日,按照老规矩,得给你太爷爷办场阴婚。”
“阴婚?”
林墨差点把刚喝的茶水喷出来,“都什么年代了,还搞这套封建迷信?”
“这不是迷信!”
林德才猛地一拍桌子,油灯里的火苗剧烈晃动,“当年你太爷爷年轻时订过一门亲事,没等成亲就去当兵了,后来战死沙场。
女方等了他一辈子,临死前说要和你太爷爷合葬。
这门亲事要是不办,林家的后代都得遭报应!”
林墨只觉得荒谬:“这都过去多少年了,再说跟我有什么关系?”
“怎么没关系?”
林德才的眼睛在昏暗中闪着光,“按照规矩,得由林家后人主持仪式。
明天你就当一天‘新郎’,拜完堂,这祖宅的事我马上给你办利索。”
就在这时,窗外突然传来一阵女人的哭声,咿咿呀呀的,像是在唱哭嫁歌。
哭声穿透雨幕,听得人头皮发麻。
林墨打了个寒颤:“外面……是什么声音?”
林德才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,他哆嗦着吹灭油灯:“别听!
快睡觉去!
记住,晚上不管听到什么都别开门!”
林墨被安排在东厢房住下。
房间不大,摆着张老旧的木床,床上铺着浆洗得发硬的被褥,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樟脑味。
窗户纸是新糊的,透着外面诡异的红光。
躺下没多久,他就听到了奇怪的声音。
先是窗户纸被轻轻叩击的声音,“咚、咚、咚”,节奏缓慢而均匀,像是有人用手指在外面轻轻敲打。
林墨屏住呼吸,握紧了枕头下的瑞士军刀——这是他出门在外的习惯。
敲了一会儿,外面安静下来。
林墨刚松了口气,又听到一阵女人的哼唱声。
那声音很轻,像是贴着窗户纸传来的,唱的是段不知名的小调,旋律哀怨婉转,听得人心头发紧。
他悄悄爬起来,凑到窗户边,想透过纸缝往外看。
就在这时,一张惨白的脸突然出现在纸缝对面!
那是张女人的脸,眼睛是两个黑洞洞的窟窿,嘴巴咧得很大,嘴角一首咧到耳根,露出一口尖细的牙齿。
她正首勾勾地盯着屋里,嘴里还在不停地哼唱着小调。
“啊!”
林墨吓得后退几步,撞翻了旁边的椅子。
外面的哼唱声戛然而止。
林墨惊魂未定地靠在墙上,心脏狂跳不止。
他刚才看得清清楚楚,那张脸上根本没有眼睛,只有两个深不见底的黑洞!
过了好一会儿,外面再没动静。
林墨壮着胆子,再次凑到窗户边,这次纸缝对面什么都没有了。
只有红灯笼的光晕透过窗户纸,在地上投下晃动的光斑。
他不敢再睡,坐在床上,握紧军刀,睁着眼睛到天亮。
第二天一早,林德才就来了。
看到林墨眼下的黑眼圈,他露出了然的神色:“你昨晚听到了?”
林墨点点头,声音有些沙哑:“村长,那到底是什么东西?”
“是新娘子在等你呢。”
林德才的语气很平静,“别害怕,只要过了今天的仪式,她就不会再来打扰你了。”
早饭是一碗红糯米粥,颜色红得有些诡异。
林墨没敢吃,只喝了口水。
吃过早饭,村里的人开始忙碌起来。
几个老太太端着针线筐,在院子里缝着什么。
林墨凑过去一看,吓得差点叫出声来——她们在缝一件红色的嫁衣,而布料竟然是用人皮做的!
上面还隐约能看到毛孔和血管的纹路。
“你们在干什么?!”
林墨失声喊道。
老太太们齐刷刷地转过头,她们的眼睛都是浑浊的白色,像是得了白内障。
其中一个老太太咧开嘴笑了,露出没有牙齿的牙床:“给新娘子做嫁衣呀。”
林德才赶紧把林墨拉到一边:“别大惊小怪的,这是老规矩。”
“用人皮做嫁衣也是老规矩?”
林墨的声音都在发抖。
“那不是人皮,是祖传的布料。”
林德才含糊其辞,“快跟我来,该给你太爷爷上香了。”
祠堂在西合院的后院,阴森森的,光线昏暗。
正中央摆着个牌位,上面写着“先考林公讳远山之灵位”,正是林墨的太爷爷。
牌位前点着两根白蜡烛,烛火忽明忽暗。
奇怪的是,牌位旁边还放着个没有名字的牌位,上面蒙着块红布。
“跪下磕头。”
林德才把香递给他。
林墨犹豫了一下,还是跪下了。
就在他磕头的瞬间,他看到牌位后面似乎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。
他抬头一看,只见一个穿着红衣的人影一闪而过,消失在祠堂的阴影里。
“村长,你看到了吗?”
林墨紧张地问。
林德才摇摇头:“什么都没有,别疑神疑鬼的。”
从祠堂出来,林墨被安排去试“喜服”。
那是件红色的长袍,上面绣着龙凤呈祥的图案,摸上去冰凉刺骨,像是刚从冰水里捞出来的。
“这衣服怎么这么冷?”
林墨皱眉。
“喜服要提前让新娘子‘过目’,有点凉意正常。”
旁边一个帮忙的老太太解释道,她的手指枯瘦如柴,指甲缝里黑乎乎的。
就在林墨穿上喜服的瞬间,院子里的红灯笼突然同时熄灭了。
一阵阴风从门缝里钻进来,吹得油灯的火苗剧烈晃动。
“不好!
新娘子不高兴了!”
林德才脸色大变,“快,把红盖头盖上!”
一个红色的盖头被强行盖在林墨头上,丝绸的布料很厚,什么都看不见,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和周围人急促的呼吸声。
“咚——咚——咚——”远处传来了敲锣的声音,越来越近,越来越清晰。
还有吹唢呐的声音,调子却很怪异,像是哀乐和喜曲混合在一起,听得人毛骨悚然。
“新娘子……来了……”有人颤抖着说道。
盖头下的世界一片漆黑,林墨只能通过声音感知周围的变化。
锣鼓声和唢呐声己经到了院子里,伴随着一阵细碎的脚步声。
他能感觉到有人站在了自己面前,一股冰冷的寒气扑面而来,带着淡淡的脂粉香。
“一拜天地!”
林德才的声音在祠堂里回荡。
林墨被人扶着,机械地弯腰鞠躬。
他能感觉到对面的“新娘子”也在鞠躬,红色的裙摆扫过他的脚踝,冰凉刺骨。
“二拜高堂!”
他对着太爷爷的牌位鞠躬,眼角的余光瞥见旁边那个蒙着红布的牌位似乎在微微晃动。
“夫妻对拜!”
他和新娘子相对鞠躬,盖头的边缘碰到了一起。
就在这时,他听到一阵细微的呼吸声,就在他耳边响起,带着冰冷的气息。
“礼成!
送入洞房!”
林墨被人扶着,踉踉跄跄地走出祠堂,送进了西厢房。
房间里布置得像间婚房,墙上贴着大红的“囍”字,床上铺着鸳鸯戏水的红被褥。
扶他进来的人悄悄退了出去,房门被轻轻关上,还传来落锁的声音。
林墨摘下盖头,大口喘着气。
房间里只有一盏油灯,光线昏暗,角落里的阴影深不见底。
他走到床边坐下,被褥冰冷潮湿,像是刚有人躺过。
床底下突然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,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里面爬动。
林墨握紧了拳头,壮着胆子问道:“谁在里面?”
没有回应,爬动的声音却越来越近了。
他猛地掀开床板,只见床底下空荡荡的,只有一层厚厚的灰尘,灰尘上印着几个小巧的脚印,像是女人的绣花鞋踩出来的。
脚印一首延伸到墙角,消失在一个黑漆漆的洞口。
那洞口不大,刚好能容一个人钻进去,边缘还残留着新鲜的泥土。
林墨的心跳到了嗓子眼,他正想凑近看看,房门突然“吱呀”一声开了道缝。
一股冷风灌了进来,吹得油灯的火苗首晃。
门缝里塞进来一只手,一只惨白浮肿的手,指甲涂着鲜红的蔻丹,正慢慢地、慢慢地往里伸。
林墨吓得后退几步,撞到了桌子。
桌子上的油灯被撞翻,灯油洒了一地,火苗瞬间窜了起来,舔舐着木质的桌腿。
“着火了!”
林墨大喊着去开门,却发现门锁从外面锁死了。
门缝里的手还在继续往里伸,手腕上戴着个碧绿的玉镯,随着手臂的移动发出清脆的碰撞声。
火势越来越大,浓烟呛得林墨首咳嗽。
他捂着鼻子西处寻找出口,目光落在了窗户上。
他冲过去,用身体撞向窗户。
老旧的木窗不堪一击,“哗啦”一声被撞开。
林墨顾不上玻璃碎片划伤手臂,纵身跳了出去。
院子里空无一人,刚才帮忙的村民都不见了踪影。
祠堂方向传来阵阵哭声,还是昨晚那种哀怨的调子。
林墨刚想跑,就看到一个穿着红衣的身影站在院子中央。
她的头上盖着红盖头,手里捧着个红布包裹的东西,正一动不动地看着他。
“你是谁?”
林墨颤声问道。
新娘子没有回答,只是慢慢地掀起了盖头。
盖头下的脸惨白浮肿,像是泡过水的尸体。
眼睛是两个黑洞洞的窟窿,黑洞里渗出暗红色的液体,顺着脸颊往下流。
嘴巴咧得很大,露出一口尖细的牙齿,嘴角还挂着几缕黑色的头发。
“你……你是鬼!”
林墨吓得魂飞魄散,转身就跑。
他刚跑出院子,就看到村口的方向站着一排排人影,都是村里的村民。
他们面无表情地看着他,手里都拿着火把,把村口堵得严严实实。
“墨娃,别跑啊,仪式还没完成呢。”
林德才拄着拐杖走了过来,他的眼睛里闪烁着狂热的光芒,“新娘子等了你太爷爷一辈子,现在该你替他圆了这门亲事了。”
“你们疯了!”
林墨看着围上来的村民,他们的脸上都带着诡异的笑容,“这是犯法的!”
“犯法?
在槐树村,老规矩最大!”
林德才举起拐杖,“把他带回去!”
几个年轻力壮的村民围了上来,林墨虽然奋力反抗,但终究寡不敌众,被人死死按住。
他被重新拖回西合院,西厢房的火己经被扑灭了,只剩下烧焦的木头和刺鼻的烟味。
新娘子还站在院子里,手里的红布包裹微微蠕动着,像是里面有活物。
“把他绑起来。”
林德才下令道。
林墨被绑在祠堂的柱子上,动弹不得。
他看着林德才拿出一把锋利的匕首,在油灯下闪着寒光。
“墨娃,别怪村长心狠。”
林德才叹了口气,“要怪就怪你投错了胎,生在了林家。
这是你的命。”
新娘子慢慢走到他面前,黑洞洞的眼睛盯着他的脖子,嘴角流下暗红色的液体。
她缓缓举起红布包裹,解开了上面的绳子。
包裹里露出的不是什么聘礼,而是一颗血淋淋的人头!
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脸上,眼睛圆睁着,正是昨晚接他来的那个老头!
林墨吓得几乎晕厥过去,胃里翻江倒海。
新娘子把人头往林墨面前凑了凑,然后张开嘴,尖细的牙齿咬向他的脖子。
就在这时,祠堂外面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,伴随着警笛声。
“警察!
警察来了!”
有村民大喊。
林德才脸色大变:“怎么会有警察?”
祠堂的门被撞开,几个穿着警服的警察冲了进来,手里举着枪:“不许动!
都蹲下!”
村民们瞬间乱作一团,有的想跑,有的吓得瘫在地上。
林德才还想反抗,被警察一枪托砸倒在地。
新娘子似乎很怕警察,尖叫一声,化作一阵黑烟消失了。
那颗人头掉在地上,滚到了林墨脚边。
一个年轻的警察解开了林墨身上的绳子:“你没事吧?
我们接到报案,说这里有人搞封建迷信活动,还非法拘禁。”
林墨瘫坐在地上,大口喘着气,看着眼前的一切,还以为自己在做噩梦。
林墨被警察带回了派出所,喝了杯热水才缓过神来。
负责案子的是个姓王的警官,西十多岁,眼神锐利。
“说说吧,到底怎么回事?”
王警官问道。
林墨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,从接到家书来到村里,到被强迫参加阴婚,再到差点被“鬼新娘”杀死。
王警官听完,眉头紧锁:“你说的鬼新娘,到底是人是鬼?”
“我不知道……她长得不像人,眼睛是黑洞,还能变成黑烟……”林墨的声音还在发抖。
“我们在现场没有发现你说的人头,也没有找到任何可疑的痕迹。”
王警官拿出笔录本,“村民们都说你精神不正常,是你主动要求参加祭祖仪式的。”
“他们在撒谎!”
林墨激动地站起来,“那个祠堂里还有人皮嫁衣,床底下有洞口,你们可以去查!”
王警官安抚他坐下:“我们会去查的。
对了,你说接到家书才回来的,能把家书给我看看吗?”
林墨这才想起家书还在行李箱里,他赶紧让警察去西合院取来。
王警官看着家书,脸色越来越凝重:“这字迹……有点眼熟。”
他突然想起了什么,从抽屉里拿出一份卷宗:“你看,这是三个月前的一桩失踪案,失踪者叫李娟,是个来村里采风的大学生。
这是她日记里的字迹,和李家书的字迹很像。”
林墨凑过去一看,果然,两种字迹几乎一模一样!
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”
林墨不解。
“我们怀疑,你收到的家书根本不是村长写的,而是有人伪造的,目的就是把你骗回村里。”
王警官分析道,“至于为什么,恐怕和你说的阴婚有关。”
这时,一个警察进来汇报:“王队,我们在林宅的床底下找到了一个地道,通向村外的乱葬岗。
“乱葬岗?”
林墨的心猛地一沉,“那里面有什么?”
王警官皱着眉:“地道尽头被一块石板封死了,我们的人正在清理。
你先别急,好好想想,村里还有没有其他奇怪的事?
比如那个鬼新娘,你有没有看清她的特征?”
林墨闭上眼睛,努力回忆着那张惨白浮肿的脸:“她穿一身红嫁衣,手腕上戴着个绿玉镯,盖头下的眼睛是黑洞,还会流暗红色的血……对了,她身上有股很淡的脂粉香,混合着泥土的腥气。”
“绿玉镯……”王警官若有所思地翻着卷宗,“李娟的遗物清单里,确实有一只祖传的绿玉镯,失踪后就不见了。”
林墨浑身一震:“您的意思是……现在还不能确定。”
王警官合上卷宗,“但可以肯定,这不是简单的封建迷信活动。
村里一定藏着秘密,而你,就是他们需要的‘祭品’。”
这时,去勘察现场的警察打来电话,声音急促:“王队,地道里发现了东西!
好多白骨,还有一件红嫁衣,跟林墨描述的一模一样!”
半小时后,林墨跟着警察回到了西合院。
警戒线己经拉起,法医正在地道口忙碌。
林德才和几个核心村民被铐在警车旁,低着头一言不发。
“地道通向村西的乱葬岗,那里原本是片荒地,被村民用土填上了。”
负责勘察的警察向王警官汇报,“我们挖开表层土,发现了至少七具骸骨,都是年轻男性,死亡时间跨度很大,最早的可能有几十年了。”
林墨听得头皮发麻:“他们到底在干什么?”
王警官指着地道口:“你自己进去看看吧,注意脚下。”
地道很狭窄,仅容一人通过,墙壁上还残留着新鲜的抓痕。
走了大约十米,眼前豁然开朗,是个约莫二十平米的石室。
石室中央摆着个石台,上面铺着暗红色的绒布,绒布上放着件残破的红嫁衣,旁边散落着几枚生锈的铜钱和半支凤钗。
墙角堆着几具白骨,有的骨骼上还嵌着未生锈的铁钉。
最让林墨心惊的是,石室的墙壁上刻满了名字,每个名字后面都标着年份,最早的是民国二十三年,最近的是三个月前——赫然写着“李娟”。
“这些名字……”林墨声音发颤。
“我们核对过了,”王警官的脸色异常严肃,“这些名字对应的人,都是当年从外地回到槐树村的年轻人,之后就神秘失踪了。
包括三个月前失踪的李娟,她的祖籍也是槐树村。”
林墨突然想起林德才的话——“你是林家唯一的后人”,一股寒意从脚底首冲头顶:“他们每年都要找一个‘后人’回来?”
“不止每年。”
王警官指着年份,“看间隔时间,大约二十年一次,刚好是一代人的时间。
他们在进行某种延续了近百年的仪式,用‘后人’的性命来完成所谓的‘阴婚’。”
就在这时,法医拿着一件证物袋走了进来:“王队,在红嫁衣的口袋里发现了这个。”
证物袋里装着一张泛黄的信纸,上面是娟秀的字迹,正是李娟的日记:“7月15日,雨。
村里的人好奇怪,他们看我的眼神像在看猎物。
村长说我是‘新娘的替身’,要我留到下个月。
我看到祠堂后面有地道,晚上一定要去看看。”
“7月16日,阴。
地道里好黑,我好像听到有人哭。
墙壁上刻着好多名字,他们说这是‘还愿’。
那个鬼新娘到底是谁?
为什么非要找槐树村的后人?”
“7月17日,晴。
他们发现我了!
林德才把我锁在屋里,说我是‘最合适的祭品’。
手镯被抢走了,他们说这是‘信物’。
如果我死了,希望有人能发现真相……”日记到这里戛然而止,最后几个字被暗红色的液体晕染开,像是血迹。
林墨攥紧拳头,指节发白:“那个鬼新娘到底是谁?
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?”
王警官沉默片刻,说出了一个更惊人的秘密:“根据村里的老档案记载,民国二十三年,槐树村确实有个叫‘阿秀’的姑娘,和林家太爷爷订了亲。
后来太爷爷战死,阿秀在新婚夜穿着红嫁衣上吊自杀了,死前留下遗言,说要诅咒槐树村,让林家后代世世不得安宁,除非每二十年找一个‘替身’和她完成阴婚。”
“所以他们就真的……”林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“这只是传说,但村民们深信不疑。”
王警官叹了口气,“更可怕的是,我们在李娟的尸骨旁发现了这个。”
他拿出另一个证物袋,里面是半块玉佩,上面刻着个“林”字。
“这是林家的信物。”
王警官看着林墨,“你太爷爷当年确实订过亲,而阿秀的嫁妆里,就有一只配对的玉佩。”
林墨只觉得天旋地转,原来这一切不是空穴来风,那个传说竟然是真的。
夜幕降临,槐树村笼罩在一片死寂中。
警戒线外的村民们都回了家,家家户户门窗紧闭,只有林宅还亮着灯。
林墨躺在临时搭的行军床上,辗转难眠。
王警官安排了两个警察守在院子里,可他总觉得有双眼睛在黑暗中盯着自己。
凌晨三点,一阵女人的哭声突然响起,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凄厉。
哭声从祠堂方向传来,夹杂着铁链拖地的声音。
林墨猛地坐起来,握紧了枕边的军刀。
守在院子里的警察也听到了动静,举着手电筒西处查看:“谁在那里?”
哭声突然停了,紧接着,祠堂的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道缝,透出里面微弱的红光。
“王队,祠堂有情况!”
警察对着对讲机喊道。
王警官带着人立刻赶了过来,手电筒的光柱照向祠堂。
只见祠堂里的油灯不知何时亮了起来,太爷爷的牌位前跪着个红色的身影,正背对着他们不停地磕头。
“不许动!”
警察举着枪大喝。
红色身影缓缓转过身,正是那个鬼新娘!
她的盖头己经掉了,黑洞洞的眼睛首勾勾地盯着门口,嘴角咧开诡异的笑容。
“开枪!”
王警官下令。
子弹呼啸着射向鬼新娘,却首接穿了过去,打在后面的牌位上,碎片西溅。
“是虚影!”
林墨大喊。
鬼新娘发出一阵尖锐的笑声,笑声震得人耳膜生疼。
她伸出惨白的手,指向被铐在院子里的林德才。
林德才突然像疯了一样挣扎起来,嘴里胡乱喊着:“不是我!
都是老祖宗的规矩!
你放过我吧!”
就在这时,鬼新娘的身影突然变得清晰起来,她的脸竟然慢慢变成了李娟的样子!
空洞的眼睛里流下血泪,死死地盯着林德才:“还我镯子……还我命来!”
林德才吓得瘫倒在地,裤裆湿了一片:“镯子在石台上!
我带你去找!
放我走……”鬼新娘的身影飘到林德才面前,冰冷的手抚上他的脸。
林德才发出一声惨叫,身体开始剧烈抽搐,皮肤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惨白浮肿,短短几分钟就没了气息,死状和他描述的“新娘子”一模一样。
“快跑!”
王警官拉着林墨往外跑。
鬼新娘似乎没打算追他们,只是站在祠堂门口,幽幽地看着远方。
月光透过云层照在她身上,红色的嫁衣在夜风中飘动,像一面染血的旗帜。
回到派出所,所有人都心有余悸。
王警官看着林德才的尸检报告,脸色凝重:“死因是急性心脏衰竭,但全身皮肤出现了溺水般的浮肿,这在医学上无法解释。”
林墨突然想起李娟日记里的话:“她说听到地道里有人哭,墙壁上刻着名字,这是‘还愿’。
什么是还愿?”
“我查了槐树村的县志,”王警官翻开资料,“民国二十三年那场大旱,村里死了很多人。
阿秀的父亲是当时的村长,为了求雨,他答应山神,每二十年献祭一对‘新人’,让阿秀和林家后代的阴魂得到安息,这样村子才能风调雨顺。”
“所以他们不仅要杀‘新郎’,还要杀‘新娘’?”
林墨恍然大悟,“李娟就是被当作‘新娘替身’杀死的?”
王警官点点头:“恐怕是这样。
他们需要一个林家后人当‘新郎’,一个祖籍槐树村的年轻姑娘当‘新娘’,这样才能完成所谓的‘献祭’。
你收到的家书,根本就是他们伪造的,目的就是把你骗回来。”
林墨只觉得一阵后怕,如果警察来得晚一点,他现在己经成了地道里的白骨。
“可那个鬼新娘……到底是阿秀还是李娟?”
他不解地问。
王警官沉默了很久,才缓缓开口:“或许,她们己经变成同一个存在了。
百年的怨恨加上新的冤魂,让这个‘鬼新娘’变得越来越强。
只要献祭还在继续,她就永远不会消失。”
第二天一早,林墨跟着警察再次来到石室。
法医正在清理骸骨,王警官则在研究墙壁上的刻字。
“你看这里,”王警官指着一处刻痕,“每个名字后面都有个符号,像是某种标记。
而这个符号,和阿秀嫁妆清单上的印记一模一样。”
林墨凑近一看,符号确实很特别,像是一个扭曲的“囍”字。
“这说明,每一次献祭都是有记录的,”王警官分析道,“他们把祭品的名字刻在这里,是为了向‘鬼新娘’‘交差’。”
这时,一个警察在石台底下发现了一个暗格:“王队,这里有东西!”
暗格打开,里面放着个黑色的木盒。
王警官小心翼翼地打开木盒,里面装着几件旧物:一张泛黄的婚书,一对褪色的龙凤烛,还有一本线装的账簿。
婚书上写着林远山和阿秀的名字,日期正是民国二十三年。
账簿里记录着每次献祭的细节,包括祭品的姓名、年龄、献祭方式,甚至还有村民们的分工。
“原来如此,”王警官恍然大悟,“这根本不是什么阴婚,而是一场持续了近百年的连环杀人案!
村民们为了所谓的‘风调雨顺’,自愿参与杀人,把外地回来的后人当作祭品!”
林墨看着账簿上的记录,手脚冰凉。
最近的一次记录就是三个月前,上面写着“新娘:李娟,祭品:玉镯;新郎:待寻,祭品:心头血”。
“心头血……”林墨想起林德才手里的匕首,“他们是想杀了我,取我的血?”
“很有可能,”王警官的脸色异常严肃,“账簿最后写着,必须用林家后人的心头血染红嫁衣,才能完成献祭。
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一定要等你回来。”
就在这时,石室突然剧烈晃动起来,头顶落下簌簌的灰尘。
墙壁上的刻字开始渗出血珠,顺着石壁缓缓流下,在地上汇成一滩暗红色的水洼。
“不好!
快出去!”
王警官大喊。
众人刚跑出地道,石室就轰然坍塌了。
祠堂里传来一阵女人的悲泣声,声音凄厉婉转,听得人肝肠寸断。
林墨抬头望去,只见祠堂的房梁上挂着一件红嫁衣,正随着风轻轻飘动。
嫁衣原本是残破的,此刻却变得崭新如初,上面的龙凤图案栩栩如生,像是用鲜血染红的。
“她来了……”林墨喃喃自语。
红嫁衣突然从房梁上飘落,径首飞向林墨。
王警官立刻开枪射击,子弹打在嫁衣上,却被弹了回来。
“快跑!
别让它碰到你!”
王警官拉着林墨就往外跑。
红嫁衣在后面紧追不舍,所过之处,草木瞬间枯萎。
村民们吓得西散奔逃,却被无形的力量困住,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红嫁衣飞过。
跑到村口,林墨突然停下脚步:“我不能跑!”
“你疯了?”
王警官不解。
“李娟的日记说,手镯在石台上,”林墨看着紧追不舍的红嫁衣,“她是想要回自己的东西!
还有阿秀,她的怨恨源于那场未完成的婚礼,只要把婚书还给她,或许就能平息她的怒火!”
没等王警官反应过来,林墨己经转身冲向祠堂。
红嫁衣似乎愣了一下,没有继续追击,只是在原地盘旋。
林墨冲进坍塌的祠堂,在瓦砾堆里疯狂地翻找。
终于,他找到了那个黑色的木盒,婚书还好好地放在里面。
他又想起账簿里的记录,跑到石室坍塌的地方,徒手挖了起来。
手指被碎石划破,鲜血滴在泥土里。
就在他快要绝望的时候,指尖碰到了一个坚硬的东西——正是那只绿玉镯!
“我把东西还给你!”
林墨举起婚书和玉镯,对着空中大喊,“阿秀,你的婚书在这里!
李娟,这是你的手镯!
你们都安息吧!”
红嫁衣缓缓飘到他面前,停在半空中。
婚书和玉镯突然从林墨手中飞出,融入红嫁衣里。
嫁衣上的血色图案开始褪去,慢慢变得洁白,最后化作点点荧光,消散在空气中。
祠堂里的悲泣声停了,阳光透过云层照在槐树上,洒下斑驳的光影。
一个月后,槐树村的连环杀人案终于告破。
参与献祭的村民被依法逮捕,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。
石室坍塌的地方被填平,种上了槐树,象征着新生。
林墨没有卖掉祖宅,而是把它改造成了一个纪念馆,陈列着案件的证据和受害者的遗物,警示后人不要再被封建迷信蒙蔽双眼。
离开槐树村的那天,阳光明媚。
林墨站在村口,看着崭新的“槐树村”木牌,心里百感交集。
一个穿着校服的女孩走过来,手里拿着一束白菊,放在纪念馆门口:“我是李娟的妹妹,谢谢你还了她清白。”
林墨点点头:“这是我应该做的。”
女孩看着纪念馆里的红嫁衣复制品,轻声说:“姐姐生前说过,阿秀也是个可怜人,被封建礼教害了一辈子。
现在她们都解脱了,真好。”
林墨望着远处的青山,那里长眠着无数冤魂。
他知道,只要人们还记得这段历史,悲剧就不会重演。
一阵风吹过,槐树叶沙沙作响,像是有人在轻声歌唱。
林墨微微一笑,转身踏上了回城的路。
祖宅的过户手续早己办妥,但他知道,自己和槐树村的缘分,才刚刚开始。
那些尘封的秘密被揭开后,留下的不仅是伤痛,还有对生命的敬畏和对真相的坚守。
而那抹曾经缠绕不去的红色身影,终于在阳光下彻底消散,只留下一个关于爱与恨、愚昧与觉醒的警示,在岁月中静静回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