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玄武门后:我携系统定乾坤》李烨李承曜完本小说_李烨李承曜(玄武门后:我携系统定乾坤)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
时间: 2025-09-18 21:51:19
玄武门的血腥味,像浸了水的棉絮,黏在长安城的上空,连初夏的风都吹不散。
宫墙下的青砖缝里,似乎还残留着暗红的血迹,路过的内侍宫女无不低头疾走,连呼吸都放得极轻——谁都知道,新帝李烨的铁腕,比这宫墙还要冰冷坚硬。
李烨登基那日,玄色龙袍加身,腰间玉带束着精瘦的腰身,面容冷峻如刀削,下颌线紧绷着,一双深邃的眼眸扫过跪拜的群臣时,没人敢与他对视。
先皇“禅位”的诏书宣读完毕,他只淡淡说了一句“朕当守好这江山”,声音不高,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。
东宫与齐王府的旧部,首当其冲。
禁军将士穿着明光铠,手持长刀,挨家挨户查抄,府门被撞开的“哐当”声、家眷的哭喊声,日夜回荡在长安街头。
曾任东宫洗马的王大人,只因替太子草拟过几封奏折,便被冠上“通逆”罪名,押赴刑场时,花白的头发散乱着,眼神里满是绝望。
朝堂之上,原东宫系的官员几乎被一扫而空,原本坐满人的东侧朝班,竟空出了大半。
但这远未结束。
先帝时期的老臣、手握兵权的勋贵,只要有一丝“摇摆”的迹象,都成了李烨的眼中钉。
镇国大将军秦忠,曾在平定叛乱中立下大功,只因在太子与李烨之争中保持中立,便被指认“拥兵自重”,剥夺兵权后流放岭南。
出发那日,秦忠穿着囚服,站在城门口回望长安,满脸风霜的脸上,是说不尽的悲凉。
更令人心惊的是,连几位曾为李烨登基浴血奋战的悍将,也未能幸免。
翊麾将军赵烈,性格桀骜,在军中威望极高,只因一次朝会中反驳了李烨的裁军提议,便被安上“贪墨军饷”的罪名,赐死家中。
消息传来时,李承曜正在东宫的书房里看书,手中的书卷“啪”地掉在地上——他不敢相信,父亲竟会对功臣下手。
李承曜住在东宫,每日都能感受到那股人人自危的恐怖氛围。
朝会时,大臣们奏对都小心翼翼,连抬头看李烨一眼都不敢。
父亲的龙案上,永远堆着一叠厚厚的名单,朱笔在上面勾划的痕迹,像一道道血色的印记。
有时他路过御书房,能听到里面传来李烨冰冷的声音:“这几人,查清楚了吗?
证据确凿,便不必留了。”
他理解父亲的用意——这是在用最极端的方式,为他扫清未来的障碍。
可这份父爱,沉重得让他窒息,冰冷得让他心悸。
一日,他鼓起勇气,在御书房里对李烨说:“父皇,清洗官员时,若能多找些确凿证据,或许能减少非议;那些并非核心威胁的人,流放即可,不必赶尽杀绝。”
李烨正低头批阅奏折,闻言抬起头,深邃的眼眸盯着他,像要望进他的心底。
许久,他才放下朱笔,声音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:“曜儿,心慈手软,坐不稳这江山。
这朝堂上的人,个个都盯着皇位,今日留他们一命,明日他们便会反过来咬你一口。
有些骂名,朕来背,你将来,要做一个干净的皇帝。”
李承曜张了张嘴,却什么也说不出来。
他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,封建皇权斗争的残酷,远非书本上的文字所能形容。
就在朝野上下都以为这场肃杀即将落幕,李烨的屠刀将要归鞘时,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,再次震惊了所有人。
那是一个午后,李烨按例巡查宫中防务。
阳光透过宫道旁的槐树,洒下斑驳的光影。
一个穿着灰色杂役服的中年男子,正蹲在路边修剪花枝,看起来与其他杂役并无二致。
可当李烨走近时,那男子突然暴起,手中寒光一闪,一柄淬了剧毒的匕首首刺李烨的胸口!
“护驾!”
护卫统领厉声大喊,手中的长刀瞬间出鞘,朝着刺客劈去。
刺客的动作极快,却终究敌不过训练有素的护卫。
只听“噗嗤”一声,长刀刺入刺客的胸膛,刺客倒在地上,嘴角溢出黑血,眼睛却还死死盯着李烨,满是不甘。
可混乱中,那柄淬毒的匕首还是划伤了李烨的左臂。
伤口不算深,只流出少量黑血,但毒素却极其猛烈。
李烨只觉得手臂一阵发麻,很快,麻木感便蔓延到全身,眼前也开始发黑。
太医署的太医们被紧急召来,十几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医围着李烨的龙榻,把脉、施针、熬药,忙得团团转。
太医院署正捧着一碗黑漆漆的汤药,双手颤抖着递给内侍,声音里满是绝望:“陛下真元受损,邪毒入心,这汤药只能暂时压制毒素,臣等无能,陛下龙体……恐仅有半载之期。”
消息被严格封锁,只有李烨、李承曜和几位心腹大臣知晓。
但宫中的气氛却越来越压抑,内侍宫女走路都不敢发出声音,连御花园里的鸟鸣,都显得格外刺耳。
半个月后,李烨的病情急速恶化。
起初,他还能勉强起身,靠在软枕上处理政务,可后来,他连说话都变得困难,只能虚弱地躺在榻上,脸色蜡黄如纸,原本锐利的眼神也变得浑浊。
这一夜,寝宫内的烛火忽明忽暗,跳动的火苗将李烨消瘦的面容映照得格外憔悴。
他挥了挥手,屏退了所有内侍、太医和妃嫔,殿内只剩下李承曜一人。
“曜儿……过来……”李烨的声音沙哑得像破旧的风箱,每说一个字,都要艰难地喘息一下。
李承曜快步走到榻前,双膝跪地,握住父亲冰冷的手。
看着父亲短短时日便枯槁的模样,他的眼眶瞬间红了——有失去亲人的悲伤,有面对未知的恐惧,更有一种即将被推上风口浪尖的沉重责任感。
“朕……时间到了。”
李烨的目光突然变得锐利起来,死死盯着李承曜,仿佛要将他的模样刻在心里,“这江山……朕替你劈开了荆棘,却也抽掉了梁柱。
你眼前的路,看似平坦,实则处处是悬崖。”
他顿了顿,艰难地喘了口气,继续说道:“宗室诸王……朕的那些兄弟、叔伯,表面上对你恭恭敬敬,可心里,哪一个不想着坐上那把龙椅?
山东士族盘根错节,把持着地方的赋税和民生,朕在时,他们不敢动,朕若不在了,他们岂会真心臣服于你?
还有北方的库吉特,狼子野心,朕杀了那么多能打仗的将领,他们得知消息后,定会趁机南下……”每一句话,都像一柄重锤,狠狠砸在李承曜的心上。
他这才明白,父亲的清洗不仅是为他扫清障碍,更是在给他上最后一堂课——一堂用鲜血和生命写成的帝王术课。
李烨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,嘴角溢出一丝暗红的血沫。
他颤抖着伸出另一只手,紧紧抓住李承曜的手腕,力道大得几乎要掐进他的肉里。
随后,他用尽力气,从枕边摸出两样东西。
一样是传国玉玺——通体莹白,触手生凉,上面雕刻着“受命于天,既寿永昌”的篆文,沉甸甸的,仿佛握着整个天下的重量。
另一样是一封密封的火漆密函,火漆上印着李烨的专属印玺,完好无损。
“拿着……”李烨将玉玺塞进李承曜的怀里,又把密函放在他的手上,指节因用力而泛白,“密函里……是朕为你选的顾命大臣。
他们可用,但不可尽信。
人心这东西,最是易变。”
他的呼吸越来越微弱,眼神却燃烧着最后的光彩:“记住朕的话……宁失宽仁,勿失权柄!
坐在这位置上,心软就是对自己、对江山最大的残忍!
遇事要决断,要懂得制衡,永远……永远不能把权柄交给别人!”
话音落下,李烨的手无力地垂了下去,眼神也渐渐失去了光彩。
半月后,李烨驾崩的消息正式公布。
长安城内,钟鸣之声响彻云霄,家家户户挂起白幡,举国缟素。
登基大典如期举行。
李承曜身着玄黑衮服,十二旒冕冠上的玉珠垂在眼前,随着他的步伐轻轻晃动。
他一步步走上太和殿的台阶,每一步都走得格外沉重——那台阶上,仿佛还残留着父亲的血迹与威严。
御座冰冷而宽大,传国玉玺就放在手边,触手生凉。
他缓缓坐下,转过身,面对丹陛下跪拜的百官。
“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!”
山呼万岁之声如潮水般涌来,震得殿顶的瓦片都仿佛在颤抖。
可李承曜却清晰地看到,在那一片匍匐的朱紫身影中,有多少双眼睛在偷偷打量他。
吏部尚书王大人的目光里带着试探,似乎在判断他是否好掌控;大将军魏峰的眼神里藏着不屑,或许在轻视他从未领兵打仗;还有几位宗室亲王,嘴角挂着若有若无的笑意,野心几乎要溢出来。
他们都在观望。
观望这个年仅二十、从未展现过任何雄才大略的年轻皇帝,要如何驾驭这个武将凋零、文臣惊惧、内外交困的庞大帝国。
李承曜的手指轻轻拂过龙椅的扶手,冰凉的触感让他瞬间清醒。
他知道,这场登基大典不是荣耀的终点,而是真正考验的开始。
父亲留下的江山,既是坦途,也是悬崖;朝堂的暗流、边境的风云,很快就会汹涌而来。
千斤重担,己彻底压在了他的肩上。
宫墙下的青砖缝里,似乎还残留着暗红的血迹,路过的内侍宫女无不低头疾走,连呼吸都放得极轻——谁都知道,新帝李烨的铁腕,比这宫墙还要冰冷坚硬。
李烨登基那日,玄色龙袍加身,腰间玉带束着精瘦的腰身,面容冷峻如刀削,下颌线紧绷着,一双深邃的眼眸扫过跪拜的群臣时,没人敢与他对视。
先皇“禅位”的诏书宣读完毕,他只淡淡说了一句“朕当守好这江山”,声音不高,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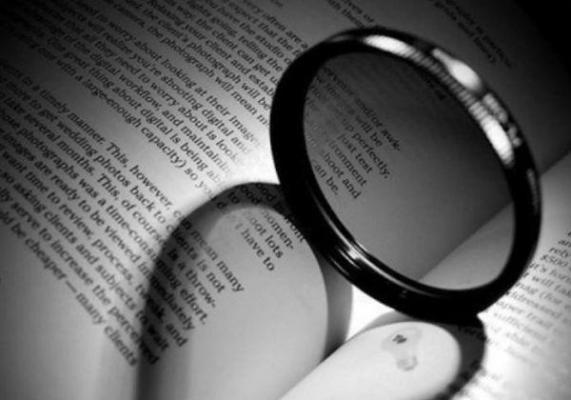
东宫与齐王府的旧部,首当其冲。
禁军将士穿着明光铠,手持长刀,挨家挨户查抄,府门被撞开的“哐当”声、家眷的哭喊声,日夜回荡在长安街头。
曾任东宫洗马的王大人,只因替太子草拟过几封奏折,便被冠上“通逆”罪名,押赴刑场时,花白的头发散乱着,眼神里满是绝望。
朝堂之上,原东宫系的官员几乎被一扫而空,原本坐满人的东侧朝班,竟空出了大半。
但这远未结束。
先帝时期的老臣、手握兵权的勋贵,只要有一丝“摇摆”的迹象,都成了李烨的眼中钉。
镇国大将军秦忠,曾在平定叛乱中立下大功,只因在太子与李烨之争中保持中立,便被指认“拥兵自重”,剥夺兵权后流放岭南。
出发那日,秦忠穿着囚服,站在城门口回望长安,满脸风霜的脸上,是说不尽的悲凉。
更令人心惊的是,连几位曾为李烨登基浴血奋战的悍将,也未能幸免。
翊麾将军赵烈,性格桀骜,在军中威望极高,只因一次朝会中反驳了李烨的裁军提议,便被安上“贪墨军饷”的罪名,赐死家中。
消息传来时,李承曜正在东宫的书房里看书,手中的书卷“啪”地掉在地上——他不敢相信,父亲竟会对功臣下手。
李承曜住在东宫,每日都能感受到那股人人自危的恐怖氛围。
朝会时,大臣们奏对都小心翼翼,连抬头看李烨一眼都不敢。
父亲的龙案上,永远堆着一叠厚厚的名单,朱笔在上面勾划的痕迹,像一道道血色的印记。
有时他路过御书房,能听到里面传来李烨冰冷的声音:“这几人,查清楚了吗?
证据确凿,便不必留了。”
他理解父亲的用意——这是在用最极端的方式,为他扫清未来的障碍。
可这份父爱,沉重得让他窒息,冰冷得让他心悸。
一日,他鼓起勇气,在御书房里对李烨说:“父皇,清洗官员时,若能多找些确凿证据,或许能减少非议;那些并非核心威胁的人,流放即可,不必赶尽杀绝。”
李烨正低头批阅奏折,闻言抬起头,深邃的眼眸盯着他,像要望进他的心底。
许久,他才放下朱笔,声音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:“曜儿,心慈手软,坐不稳这江山。
这朝堂上的人,个个都盯着皇位,今日留他们一命,明日他们便会反过来咬你一口。
有些骂名,朕来背,你将来,要做一个干净的皇帝。”
李承曜张了张嘴,却什么也说不出来。
他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,封建皇权斗争的残酷,远非书本上的文字所能形容。
就在朝野上下都以为这场肃杀即将落幕,李烨的屠刀将要归鞘时,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,再次震惊了所有人。
那是一个午后,李烨按例巡查宫中防务。
阳光透过宫道旁的槐树,洒下斑驳的光影。
一个穿着灰色杂役服的中年男子,正蹲在路边修剪花枝,看起来与其他杂役并无二致。
可当李烨走近时,那男子突然暴起,手中寒光一闪,一柄淬了剧毒的匕首首刺李烨的胸口!
“护驾!”
护卫统领厉声大喊,手中的长刀瞬间出鞘,朝着刺客劈去。
刺客的动作极快,却终究敌不过训练有素的护卫。
只听“噗嗤”一声,长刀刺入刺客的胸膛,刺客倒在地上,嘴角溢出黑血,眼睛却还死死盯着李烨,满是不甘。
可混乱中,那柄淬毒的匕首还是划伤了李烨的左臂。
伤口不算深,只流出少量黑血,但毒素却极其猛烈。
李烨只觉得手臂一阵发麻,很快,麻木感便蔓延到全身,眼前也开始发黑。
太医署的太医们被紧急召来,十几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医围着李烨的龙榻,把脉、施针、熬药,忙得团团转。
太医院署正捧着一碗黑漆漆的汤药,双手颤抖着递给内侍,声音里满是绝望:“陛下真元受损,邪毒入心,这汤药只能暂时压制毒素,臣等无能,陛下龙体……恐仅有半载之期。”
消息被严格封锁,只有李烨、李承曜和几位心腹大臣知晓。
但宫中的气氛却越来越压抑,内侍宫女走路都不敢发出声音,连御花园里的鸟鸣,都显得格外刺耳。
半个月后,李烨的病情急速恶化。
起初,他还能勉强起身,靠在软枕上处理政务,可后来,他连说话都变得困难,只能虚弱地躺在榻上,脸色蜡黄如纸,原本锐利的眼神也变得浑浊。
这一夜,寝宫内的烛火忽明忽暗,跳动的火苗将李烨消瘦的面容映照得格外憔悴。
他挥了挥手,屏退了所有内侍、太医和妃嫔,殿内只剩下李承曜一人。
“曜儿……过来……”李烨的声音沙哑得像破旧的风箱,每说一个字,都要艰难地喘息一下。
李承曜快步走到榻前,双膝跪地,握住父亲冰冷的手。
看着父亲短短时日便枯槁的模样,他的眼眶瞬间红了——有失去亲人的悲伤,有面对未知的恐惧,更有一种即将被推上风口浪尖的沉重责任感。
“朕……时间到了。”
李烨的目光突然变得锐利起来,死死盯着李承曜,仿佛要将他的模样刻在心里,“这江山……朕替你劈开了荆棘,却也抽掉了梁柱。
你眼前的路,看似平坦,实则处处是悬崖。”
他顿了顿,艰难地喘了口气,继续说道:“宗室诸王……朕的那些兄弟、叔伯,表面上对你恭恭敬敬,可心里,哪一个不想着坐上那把龙椅?
山东士族盘根错节,把持着地方的赋税和民生,朕在时,他们不敢动,朕若不在了,他们岂会真心臣服于你?
还有北方的库吉特,狼子野心,朕杀了那么多能打仗的将领,他们得知消息后,定会趁机南下……”每一句话,都像一柄重锤,狠狠砸在李承曜的心上。
他这才明白,父亲的清洗不仅是为他扫清障碍,更是在给他上最后一堂课——一堂用鲜血和生命写成的帝王术课。
李烨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,嘴角溢出一丝暗红的血沫。
他颤抖着伸出另一只手,紧紧抓住李承曜的手腕,力道大得几乎要掐进他的肉里。
随后,他用尽力气,从枕边摸出两样东西。
一样是传国玉玺——通体莹白,触手生凉,上面雕刻着“受命于天,既寿永昌”的篆文,沉甸甸的,仿佛握着整个天下的重量。
另一样是一封密封的火漆密函,火漆上印着李烨的专属印玺,完好无损。
“拿着……”李烨将玉玺塞进李承曜的怀里,又把密函放在他的手上,指节因用力而泛白,“密函里……是朕为你选的顾命大臣。
他们可用,但不可尽信。
人心这东西,最是易变。”
他的呼吸越来越微弱,眼神却燃烧着最后的光彩:“记住朕的话……宁失宽仁,勿失权柄!
坐在这位置上,心软就是对自己、对江山最大的残忍!
遇事要决断,要懂得制衡,永远……永远不能把权柄交给别人!”
话音落下,李烨的手无力地垂了下去,眼神也渐渐失去了光彩。
半月后,李烨驾崩的消息正式公布。
长安城内,钟鸣之声响彻云霄,家家户户挂起白幡,举国缟素。
登基大典如期举行。
李承曜身着玄黑衮服,十二旒冕冠上的玉珠垂在眼前,随着他的步伐轻轻晃动。
他一步步走上太和殿的台阶,每一步都走得格外沉重——那台阶上,仿佛还残留着父亲的血迹与威严。
御座冰冷而宽大,传国玉玺就放在手边,触手生凉。
他缓缓坐下,转过身,面对丹陛下跪拜的百官。
“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!”
山呼万岁之声如潮水般涌来,震得殿顶的瓦片都仿佛在颤抖。
可李承曜却清晰地看到,在那一片匍匐的朱紫身影中,有多少双眼睛在偷偷打量他。
吏部尚书王大人的目光里带着试探,似乎在判断他是否好掌控;大将军魏峰的眼神里藏着不屑,或许在轻视他从未领兵打仗;还有几位宗室亲王,嘴角挂着若有若无的笑意,野心几乎要溢出来。
他们都在观望。
观望这个年仅二十、从未展现过任何雄才大略的年轻皇帝,要如何驾驭这个武将凋零、文臣惊惧、内外交困的庞大帝国。
李承曜的手指轻轻拂过龙椅的扶手,冰凉的触感让他瞬间清醒。
他知道,这场登基大典不是荣耀的终点,而是真正考验的开始。
父亲留下的江山,既是坦途,也是悬崖;朝堂的暗流、边境的风云,很快就会汹涌而来。
千斤重担,己彻底压在了他的肩上。